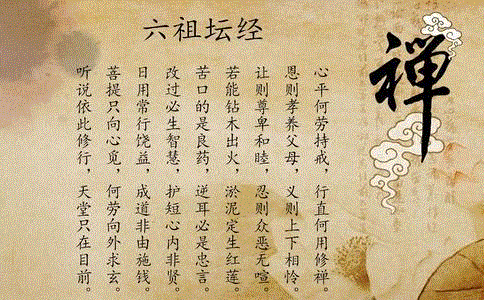蔡日新居士:希迁《参同契》浅疏
发布时间:2024-07-17 03:04:13作者:六祖坛经全文网希迁《参同契》浅疏
一、前言
石头希迁的《参同契》,词旨幽赜,读者颇为费解。而依《景德传灯录》卷十四,则当年希迁大师的《参同契》“颇有注解,大行于世“。今其注本已不复可得。《人天眼目》卷五中虽载有雪窦禅师对《参同契》的著语,恐今之读者执卷亦如蚊叮铁牛,无个入处。诸方邀愚作注,以广流传,因愧学修浅薄,未敢下笔,今戒圆法师又诚心相邀,实不得已,只得勉力为之。然犹不敢不遑恐以申数语如下,以诚心奉献于读者。
一、《参同契》的创作是希迁大师行业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它是希迁禅学思想的结晶。后人所谓“石头路滑”,事实上莫如《参同契》之圆融至无迹可寻。从某种角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领会了《参同契》便体会了“石头路滑”的内涵。非但如此,石头的《参同契》还对后世禅学思想有重大的影响。这里且莫说南岳系禅,也不去谈石头的天皇一系子孙,仅就其药山一系禅来说,无宁是石头《参同契》思想的直接传承,也可以说是《参同契》这一禅学思想的历史延伸。诸如云岩昙晟的《宝镜三味歌》、洞山良价的《玄中铭》、《新丰吟》等,都可以从《参同契》这个“母体”中找到极为直接的遗传因子。因而,研究《参同契》,不只是找对了石头的入路之门,也寻到了青原禅的源头。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个祖师传法偈,我们固然不能视若罔闻;同时也不可草率视之,以错会祖师深意。
二、佛说三法印,但站在究竟义上讲,毕竟唯一实相印,而作为这表现实相印中的胜义谛,又非文字语言可以表述得出来的,故古德宁肯终日默尔,像弘一律师那样的大德在示寂时虽如“春枝花满,天心月圆”,然而他之作偈也只是说“廓尔忘言。”禅家所谓“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即是要学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从而反躬自悟,以体胜义。以故举凡大禅师的开示皆是有语中著无语,有相中示无相,此等境界决非文字可以表现得出。即表现得出了,或者悟了,所说文字离自心之所悟尚且远矣,又何况是诠古德法偈?故尔此篇文字只是童蒙之止啼黄叶,学者须自家具正法眼,悟第一义,方会石头祖师《参同契》之深义。又恐个别于佛门外讨生活的文人,逞其笔墨。东抄西摘,活剥生吞,如此则更遗祸天下矣,是以不敢不于前言中郑重告之。
三、禅师偈颂往往著意于一“玄”字,《参同契》之卒章亦明言“参玄”二字,洞山颂五位时则更是推举“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事实上“心声只得传心了”,故尔拙疏之语不可能太实,六朝时刘彦和论作文之道尚且云“意翻空而亦奇,言微实而难巧(《文心雕龙.神思》)何况是疏注祖师玄偈呢?
二、《参同契》浅疏
《参同契》原来全称为《周易参同契》,本是道家著作。晋人葛洪《神仙传》称其为魏伯阳所作,是书旨在以《周易》、黄老、炉火三家相参同,以归于一趣而契大道也。宋人朱熹、蔡元定皆治是书,今之论者则更是汗牛充栋也。其实,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民间的经学家便附会于五经而立继学。但在汉代盛行的“七纬”中,“易纬”为《乾凿度》,而无《参同契》,这就足可见出是书纯为道家丹书。
希迁大师此偈纯是借用《参同契》为题,并非像魏伯阳那般以炉火为鹄的。在希迁大师所处的那个年代,正是佛教在东土深植根本蓬勃发展的年代,当时的佛教不但存在着各宗门间需要调燮的历史使命,而且就连禅宗内部也存在着南北各宗之间互相圆融的问题。再说,佛教要在唐土健康发展,也面临着一个与东土儒、道文化间如何处理关系的问题,面对当时中国佛教的现状,作为一代高僧,希迁大师勇敢地承担起了调燮佛教内部各种矛盾以及佛教与东土文化间矛盾的历史使命。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石头希迁作《参同契》的缘起,便可知其泰半。当时的希迁大师是在读僧肇《涅槃无名论.通古第十七》中的“会万物为已者,其唯圣人乎”一语有所感而作《参同契》的(事具《五灯会元》卷五)。这便昭示了大师将会天下圣哲之心,以成一大法幢。事实上,石头禅师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中国佛教的历史使命,大师自身的修持非但达到了“天地万物皆备于我”(《孟子》语)的境地,而且使其子孙们沿着他圆融无碍的家规健康发展,成为南禅两系巨流的一大法脉。
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
竺,姓也,取天竺之竺,其人为天竺之产,故称为竺。今按:偈中“竺土”二字连用,当取天竺之义。天竺,印度之古称,《西域记》曰:“天竺之称,异义纠纷。旧云身毒,或云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竺土即天竺地土,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佛陀降生在古印度迦毗罗卫城释迦王族的家庭里,故后人称佛教为竺土流传而来。大仙:即指佛陀。人或谓何以名佛为“仙”?今按,无伤也。一者希迁大师恒顺众生,随缘说法也:二则经论中亦可查到出处,如《金刚经》则有:“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云云,“忍辱仙人”即佛陀之前生也。何况这里称“大仙”,本来就恭敬之义具足了。“心”字则是本偈中最吃紧的字,《人天眼目》卷五所载拈花公案云世尊在灵山法会上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分付摩诃迦叶。”这里的“心”字就是指的“涅槃妙心”。自古以来,禅家以传佛心印为宗旨,故又有佛心宗之别称。“竺土大仙心”,即是指的西土佛陀的涅槃妙心。
“东西”,指佛法由西而东传。相传汉明帝因夜梦神人入殿,而遣使蔡愔、秦景等使于天竺,“愔乃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迁洛阳”,《牟子理惑论》、《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对此均有记载,故洛阳白马寺被称为中国第一伽蓝。尽管对于佛法东传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尚各持异议,但对白马寺的修建与《佛说四十二章经》的译出的史实是并无异议的,因而将佛教流传中国的时间确定为东汉永平十年(68年),应当是可靠的。“密相付”谓密相付嘱。其中一个“密”字不可淡视;一者佛法之了义是非文字言语可以说出来的,故洞山《玄中铭序》云“有句中无句”、“无语中有语”,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师徒间所传心印应是深密的。二者禅宗自达摩东传以来,皆有师徒印心并传衣钵以表信,六祖以后虽不复传衣钵,但石头一系禅的师徒印心仍存古风,香港《内明》第二十二卷则有专文论及此事(见静叶《论佛教曹洞宗与〈参同契〉、〈易经〉之关系》)。再则,云岩在《宝镜三昧歌》中发轫即云:“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洞山的《纲要偈》云:“金针双锁备”,似均反映了一种禅法与密法间的切合。固然,单纯从字面上亦可理解为佛法的胜义谛是东西密付,但可心会而不可言语的。
人根有利纯,道无南北祖。
这两句偈子是说人的根器有利钝之分,而作为佛法之胜义但有一味法,而无南北之别。事实上,三藏法典,佛说三车,皆是方便施设,学人当出化城而登彼岸,此时则但见一乘法而无二乘之见了。按:“六祖寂后,荷泽神会曾与神秀门人崇远禅师展开了一场争夺禅宗正统地位的争斗,而希迁禅师主张顿渐圆融,故以此偈语对南北二方加以规劝。事实上,希迁禅师的这一见地不但契于佛门经教,也与祖师慧能的教诲甚相契合。《坛经》云:“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又云:“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渐顿。”又云“迷即渐契,悟入顿修。”由此可见,希迁大师的此二偈语是完全禀承祖意而发的,无怪乎他在《草庵歌》(见《景德录》卷三十)中云:“遇祖师,亲训诲”,此处即可得以印证,后世云岩作《宝镜三昧歌》云:“今有顿渐,缘立宗趣,”则完全是对《参同契》思想的如是发挥。
灵源明皎洁,枝派暗相注。执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
“灵源”一语,衍乎灵根而来。因而灵根系道家语(《太玄经》云:“美厥灵根”,注云:“灵根,道德也”。)所以,希迁大师易一字而称“灵源”,但希迁大师为圆融东西土文化,使佛法深植东土,在《草庵歌》中也便用过“灵根”一词。如何理解“灵源”的含义,这倒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站在佛法广大,无所不敷洽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灵源”即是法性,亦未尝不可。况且如此理解,与本偈中后文所说的四大、五根等义亦相吻合。如果站在有情的角度上讲,我们称“灵源”为佛性,亦未尝不可,它正好与上面的那两句偈相契合。站在华严家法界缘起论上看,法性(灵源)周遍世界,它有如皎洁之明月,清晖无所不照,且又不于枝于派无不暗相流注。站在这个角度上认识灵源便是佛之本性的本体,所以它无时不在,无处不贯注,所以希迁说“圆鑑灵照于其间。”禅家的见性成道,事实上也就是要求学人对这无时不在、无处不贯洽的法性(灵源)有切身的体认(证道)。
“事”与“理”是华严宗的两个概念:“理”是渗透在千差万别的现象界事物中的本体,即法性;“事”是渗透了法性的现象界中千差万别的事物,它属于用的范畴。偈中明示学人:如果执着千差万别的某一现象界事物是属于迷惑的,另一方面仅仅只体会了寓于现象界中的法性本体也并非是了悟。那么,如何才是真正的明心见道呢?这便是本偈的下文所要论述的重点。
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
这四句是本偈的重心所在。它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门门一切境)之间的关系是“回互而又不回互”的:站在回互的角度上讲,各种事物间是相互关涉的,是统摄于法性这个本体之中的;站在不回互的角度上看,各种事物又各自住位,互不淆杂。所谓回互,是指事理无碍,事事无碍;所谓不回互,是指事理各立,事事住位。这便向学人昭示了理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而一切事物又在理这个本体的统摄下各呈差别。因而学人在把握事物的本体时,切不能昧失其现象界的差别;在认识到现象界的差别时,又不能昧失了渗透于一切现象界中的“理”。这正是古德所谓的不能因万古长空而昧却一朝风月,又不能因一朝风月而昧失万古长空之理。理事圆融,回互而又不回互,方是石头真正的“路滑”之处。
色本殊质象,声无异乐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
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
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

本段偈语从三科(蕴、处、界)法门来阐述理、事之间的“回互不回互”关系。
“色”在佛教中具有“质碍”义,它约略相当于物质的概念(即从四大义上讲),亦含有部分精神现象,站在四大和合与有情角度上讲。总之,凡是我们的六根所感受得到的质碍物,都可统称为“色”和范畴。“色本殊质象”是说人们的六根所感受的现象界事物的本来面目,与六根依缘六尘而生的六境(质碍象)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人们习惯于从自身的立场(我执)与根据以往的经验(执法)来看待世间的万物,所以,由此而产生的“质象”(对事物表象的虚妄认识),固然会与色界物的本来面目大相径庭。因而,站在佛法修证的角度上讲,如何认识纷然万法的本来面目,就有一个断二执的问题,亦即如唯识家所谓的八识转四智的修证。“声无异乐苦”是指人们的耳根所依缘声尘而生的耳识,与声尘的本来面目是大相径庭的(因二执故)。以上两句不应只孤立地停留在“色”与“声”两个方面,而应当触类而通之,由此而引伸至香、味、触、法等领域,由此而彻底地破斥六境的虚妄性。
在《参同契》中,理与事、母与子、明与暗、尊与卑,都属于超乎寻常哲理思辩的概念范畴。暗与明殆犹理与事(体与用),也如洞山当年涉水覩影时所说的“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完全是以影与形来说体与用。可见,“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之意,殆为在本体上似合符上中根机的言句,放在体用圆融的角度上去看,却又是清浊分别见之境。因而,只有如洞山似的形影冥合,方契于石头体用圆融的禅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明与暗这对禅学的范畴,发展到洞山与曹山时的五位禅法时,曾出现了以黑白来表明暗关系的现象(如正中偏,偏中正等)。这就足可见出《参同契》对后世禅学思想,尤其是对曹洞思想的影响。
“四大”在佛教中属于色阴的范畴,它指的是地、水、火、风这四大类物质(在中国则主五行说)。此外,佛教中尚有五大说(地、水、火、风、空),六大说(地、水、火、风、空、识),依著不同的经教,故有不同的立说,若依了义经,自然超乎文字言说,世间万法(一切现象界)皆是四大和合而成。地性之坚,水性之湿,火性之暖,风性之动,才是四大的自性,而又以四大因缘和合故,使其自性不能如是显现。若断除二执,透过四大和合的一切现象界事物而见到其四大和自性,则将于用中见体,也如同因子而见其母了。事实上,这里的母子喻。完全可以视为体用关系。下文的“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就是从四大的自性上来说的,也是对“四大性自复”的补充注脚。诚然,从用的角度看待法界,则有四大自性之别;若从体的角度来观照,则华竟无有自性的定法可言。
“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两句,谓眼根所对为色尘(咸醋)。耳根所对为声尘(音声),鼻根所对为香尘,舌根所对为味尘(咸醋)。在这里,希迁禅师列举了五根所对的五尘,学人也自然将会揣度出意根所对之法尘(因受韵文局限未出现)。由是,六根所对六尘而生的六境亦可想而知,以故六处、十八界法尽矣,合前者色蕴法(由此而引申为受、想、行、识五蕴),三科开示之义足矣。学人当知五蕴本空(虚妄不实),六处本无,十八界非法亦非非法,则二执意除,真如真如顿见,佛道自成也。
“然依一一法,依根叶分布”两句,正中对上文的总结。站在方便的角度上讲,故有四大、六处、十八界之分;站在究竟的角度上讲,世间纷然万法皆是一真如之所变现,皆如同由真如这个根本所派生的枝叶。若作如是观,则不昧真如之体用,亦不违石头之深深密意。
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
这两句偈语仍是紧扣回互理论而阐发的。“本末”事实上是指的体用,大师在这里明确地强调了体与用之间的回互关系必须纳入禅家的宗旨之中,而站在方便的角度上,则可以“尊卑”用其语,值得注意的是,希迁大师的“尊卑”二字给后世曹洞子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云岩的《宝镜三昧歌》中“臣奉于君,子顺于父;不顺非孝,不奉非辅”的理论,便是从希迁大师这个源头发展而成的。到了洞山五位君臣,这一思想便更为发展成熟,也几乎成了曹洞的家规。
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
这一部分偈语的旨意主要是教授门徒如何应机接人。关于明暗的概念,在上文中已述及,此处即不赘言。依著偈语,其大意殆为:在学人悟道处在用中有体时,师父则不能单纯地从体用的角度去接引他;而当学人悟道处在体中有用时,其师亦不能单纯地从用的角度去接引他。理与事各自相对待而又统一于真如之体,这便如同人在行走时两足有先有后,不可偏废一般。
希迁大师的这一理论非但影响了云岩的“宝镜三昧”思想,而且也是洞山“五位君臣”思想的直接源头。洞山的“五位偏正”理论,用黑色表示“正”(即“体”亦如本偈中的“暗”),用白色表示“偏”(即“用”,亦如本偈中的“明”),而只有在体用冥合,形影完全相切合(即是明暗相合)的境界中,才达到了五位中的“兼中到”这一最高功位。后世洞山的或从正位、或从偏位接引学人,便是从石头这一祖训中衍化开去的。说千道万,禅门祖师的这些作略,无非是教学人,圆融体用、不落有无,以步入“虚玄大道”,亦如希迁《草庵歌》之所谓“廓达灵根非向背”与“不属中间与内外”。
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
此两句偈言方世间万法各有其功用,学人当明其“用”与所用之场合。从这一观点出发,世间法纷然,不可妄立一法,亦不可妄废一法,事实上,希迁大师的禅法顿渐兼融、理事圆融、体用不昧,形成了一种十分圆成的宗风,也因为其“圆”,故学人入石头之门有针剳不入之感。
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承言须会宗,勿自方规矩。
“事”存在于“理”之体中,故尔为“理”所涵盖无遗;而理又如一竿紧接一竿急飞疾射而来的箭锋,无“事”不被它所贯串。这段文字事实上是对上文“回不互不回互”的再度重申,从而确立石头宗规。在石头时,南宗禅勃兴,各家自立规矩,使南宗禅离六祖的曹溪法席日远。而希迁大师禀六祖遗诫,为了“不失本宗”,不得不向当时日益远离曹溪宗旨的同参作出理智的规劝:你们秉承祖师言教必须理会其宗风,不得自立规矩以坏祖师家法。
“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近远,迷融山河固。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
“触目会道”犹“触目菩提”若真大修行人,已悟彻第一义,则会触目皆菩提,正所谓“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尽是法身”也。若从石头理事圆融、“回互不回互”的思想出发,何物又非真如之体的变现呢?因而学人不能当下即得,触目悟道,即非真得,这正是禅家所谓的拟议之间,咫尺千里,后世洞山《玄中铭》云:“举足下足,鸟道无殊;坐卧经行,莫非玄路”,便是从希迁这一思想发展开去的。站在“触目会道”的立场出发,“进”(悟道)途并无远近之别,一旦豁然见道,便顿悟真如;而执迷于事理之别,不明“回互不回互”之理,则人之与道相隔有如山河阻隔之坚固。为此,大师再度奉劝参禅学人,若不明“回互”的禅理,将枉坐竹榻蒲团,虚度一生时日。
在此偈的结尾,似有一个问题,仍须提出:那就是偈中将“参禅”称之为“参玄”,印顺长老认为在中国禅宗上“似乎石头是第一人”。虽然,石头禅师将禅说成“玄”,似有一点道家的风味,但也毕竟道出了石头家风幽玄的特色。石头的子孙们也就是沿着这条幽玄的道路走下去的:从药山惟俨的“石上栽花”到云岩《宝镜三昧歌》的“细入无间,大绝方所”,是可以明显地见出这种思想发展的踪迹的;到洞山作《玄中铭》,云“寄鸟道而寥空,以玄路而该括,”可谓将石头的幽玄禅风发展到了极致。
《参同契》全偈只二百二十字,但它囊括了希迁大师禅学思想的精华。若要研究石头以降的青原禅,尤其是曹洞禅,《参同契》几乎可以说是入门管钥、涉河之津梁了。在日本曹洞宗人中,将石头禅师尊为开宗先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曹洞思想是从石头这里发展开去的,曹洞是石头法脉的直接传承。为此,笔者不揣浅陋,为全偈略作义疏,以祈为修学此宗之同仁以奏铺路之功。至于未逮玄旨者,诚有俟乎达者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