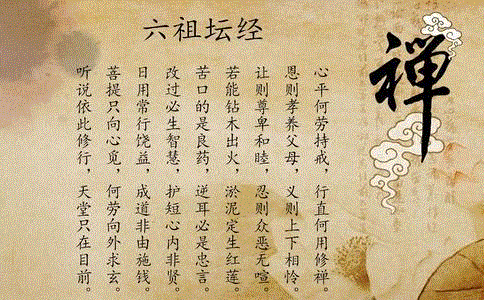略论禅宗与念佛--以四祖至六祖为中心(上)
发布时间:2022-12-01 08:44:39作者:六祖坛经全文网略论禅宗与念佛
--以四祖至六祖为中心(上)
宗舜法师文正义
内容提要:本文以中国禅宗四祖至六祖的禅学思想为中心,分“引言”、“东山法门”、“南能北秀”、“禅净融汇”四个部分,阐述了禅宗的主要禅法特点,以及对待念佛这一修行方式的态度,探讨了禅宗与净土宗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禅 禅宗 念佛 净土 净土宗
--------------------------------------------------------------------------------
引言
半个世纪前,太虚大师讲过:“中国佛学特质在禅。”(1)禅在中国佛教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但是,禅修与念佛一样,同为佛教的基本修行方式,乃各宗各派所奉行,并非独为禅宗所擅有。禅宗之所以能够开宗立派,而又名之为“禅宗”,固是以它作为彻见心性的根本途径。可是,如果与其它佛教宗派的禅修,在目的、方法以至传承上,没有自身特别之处,那就泯灭了宗门面目。禅宗的念佛,比之它宗的念佛,也不是时时事事相符合。在禅宗的历史上,修禅与念佛,其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其关系也不是唇齿相依。
在佛教中,戒、定、慧称为三学,是僧伽修行的纲要。《楞严经》说:“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2)“定”就是禅。“定”是中国固有的语词,《说文解字》:“定,安也。”(3)可知“定”的原义为安定,引申有宁静、停息的意思。梵文Samādhi,音译为三昧或三摩提、三摩地,意译则为正定、等持。音、意二种译法,在佛经中都存在。禅,《说文解字》说:“禅,祭天也。”(4)“祭天”是禅的本义,读ㄕㄞ(善音,去声)。后来在翻译佛经“Dhyānā”时被借用,变读ㄔㄞ(惭音,阳平)。《玉篇》“示部”说:“禅,静也。”(5)禅是Dhyānā的译音“禅那”的略称,意译则为静虑。在中国,二者常相并称为“禅定”(6)。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说:“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中华翻为思惟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源者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称为禅那。”(7)
佛教传入中国,禅学便与之俱来。早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由安世高、支谶、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及昙摩密多等人,译出了众多种类的禅经。他们所绍介的,大都以小乘禅法为主,如《安般守意经》、《修行道地经》、《坐禅三昧经》及《达摩多罗禅经》等。同时,大乘禅法也被绍介了过来,如《般舟三昧经》、《观无量寿经》、《首楞严三昧经》等。约在公元四、五世纪间,修禅的种种法门已经逐渐地在中国流传开来(8)。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一说:“达摩未到,古来诸家所解,皆是前四禅八定。”(9)“四禅八定”是色界天的四禅和无色界天的四无色定的合称,在印度原来属於外道所修,佛陀吸取后进行了改造。这种禅法仍属小乘禅的体系,不能导致究竟解脱。当时所流行的禅法,也不全如宗密所论,“皆是前四禅八定”,也还流行着数息观、五门禅之类的小乘禅法。南朝梁/慧皎《高僧传》的“习禅”篇,所载僧传二十一人,(10)作者在篇末《赞》里说:“五门弃恶,九次丛林。”(11)便是一个证明。
禅宗所修习的禅定属於大乘禅。小乘禅与大乘禅有什么不同?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一说:
又真性则不垢不净,凡圣无差;禅则有浅有深,阶级殊等。谓带异计欣上厌下而修者,是外道禅。正信因果亦以欣厌而修者,是凡夫禅。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禅。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上四类,皆有四色四空之异也)。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渐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展转相传者,是此禅也。(12)
禅宗的禅法“是最上乘禅”,当然地与所谓外道禅、凡夫禅的浅深、阶级不可同日而语了。禅宗的禅法的特点,被后人概括地总结为:离言说相,不著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菩提达摩怀着“传教救迷情”(13)的目的而来中土,虽被后世奉为中国禅宗初祖,而毕其一生,都未能走出屯蹇之境,其禅法也未得弘化开来。至於他的生平,包括出身、经历乃至生卒,都是充满了神秘和疑团。根据历史文献综合,我们大致地知道,达摩是在南朝宋时,泛海来到中国,比之佛教之东传,已经晚了约四百年。后来北至北魏嵩、洛一带,弘传大乘“二入四行”禅法,不为时流所见重,曾入少林寺安心壁观。达摩行头陀行,居无定址,“游化为务”。达摩的传法方式,也是“随其所止”,弟子名者仅道育、慧可等,寥寥可数。最后,“不测所终”(14)。
道宣对於达摩很推崇,说他“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15)按理说,他的“大乘壁观”禅定法,应该能够顺畅地推行。可是事与愿违,因为“于时合国盛弘讲授”,(16)达摩的禅法同时尚格格不入,以至到处受到讥谤、排挤以至打击。(17)当时讲经和注疏事业的繁荣,是随佛教经典的名相化而来的。我国初期的译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所用词语也往往借用本土老、庄及玄学之所有。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三藏逐渐被系统地介绍过来,遂产生强烈的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的要求。(18)合国盛弘讲授的风气,虽说不利达摩禅法的传播,却为下开隋唐时期的各类佛教门派,建立了广泛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达摩初履中土之不得意,可能还有其禅法上的原由。上文已经论及,当时广为流传的大都是小乘禅法,而达摩弘传的却是大乘禅法。我们读《高僧传》“习禅”篇各传,所见都是其人的神通如何广大,这既有中国六朝志怪文化的影响,也许还反映了当时行者习禅的旨趣。慧皎也说:“禅用为显,属在神通。”将禅定与仙术相属。(19)而达摩的“二入四行”,却是要趣入菩提道,销融无始以来的种种积习,以彻见自性本源为目的。在境界、方法以至目的上,都与时俗大异其趣。燕雀不知鸿鹄之志,达摩禅不为时人所接受,也是固所当然的了。
初祖达摩所遭际的屯骞境遇,也同样为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粲所亲受。禅宗在初创期间,命运惟艰,屡遭打击,居无定所,门庭寂寥。《历代法宝记》谓慧可“后佯狂,于四衢城市说法,人众甚多”,竟遭诬告,为城安县县令翟冲侃杀害。(20)《续高僧传》则说僧粲“后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滞文之徒,是非纷举”,(21)只得隐居遁世。在这种境况下,他们守成已是不易;求其发展达摩的禅法,乃不能也,非不为也。这一时期,禅宗尚未与念佛发生关系。但是,就在达摩禅郁而不彰之时,净土信仰却渐入人心。且不论在此之前弘扬弥勒净土信仰的道安、弘扬阿弥陀佛净土信仰的庐山慧远这些佛教领袖,就是与达摩同时代的净土宗重要人物昙鸾,与达摩的际遇相比,二者也是判若云泥。
昙鸾(476-542),据唐/道宣《续高僧传》记载,为雁门人(雁门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出家后广学经论,尤擅《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及佛性学说。他在为北凉/昙无谶译《大集经》作注时得气疾,因而感到生命短促,希望找到长生不死的方法。他听说江南道士陶弘景博通仙术,名重海内,便于梁大通年间(527-528)往江南寻访。起初昙鸾被人怀疑是北朝的奸细,经澄清后,被引见给梁武帝。梁武帝不仅亲自“降阶礼接”,(22)甚至称昙鸾为“肉身菩萨”,“恒向北遥礼”。(23)后来,昙鸾因菩提留支授与《观无量寿佛经》而放弃陶弘景所传仙术,专志阿弥陀佛净土信仰的修学与弘传,“自行化他郡,流靡弘广,魏主重之,号为神鸾焉。下敕令住并州大寺,晚复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时往介山之阴,聚徒蒸业,今号鸾公岩是也。”(24)昙鸾所建立的“二道二力说”、“往生成佛说”、“持名念佛说”等理论,为净土宗的广泛弘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禅宗所初期遭遇的窘迫境况,直至道信、弘忍的时代,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东山法门
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是禅宗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们所开创的“东山法门”,(25)是禅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捩点,一个里程碑,标志禅宗自此真正意义的成立。
道信(580-651),俗姓司马,河内人,(26)因其父任永宁令,全家迁徙至蕲州。(27)七岁出家。僧璨隐舒州皖公山时,往赴受法,依学十载。隋炀帝大业间,贼围吉州城七十馀日,教全城合声同念“般若”。后来留止於庐山大林寺,达十年之久。(28)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蕲州道俗请度江北,因见黄梅双峰山(29)“有好泉石”,遂造寺终止。(30)“大作佛事,广开法门,接引群品,四方龙像,尽受归依。”(31)唐贞观十七年(643),太宗三次敕使,礼请入京,均辞老不赴。(32)永徽二年闰九月示寂,春秋七十二。
道信的历史功绩,首先是北迁黄梅,辟宇授徒,对於禅宗的传承方式作了大胆的革新。此前的禅宗宗师,都是采用头陀行的个人静修方式。史载达摩及其门人“行无辙迹,动无彰记。法匠潜运,学徒默修”。(33)其门下都承其遗风,过着“住无再宿”、“常行乞食”(34)的苦行僧生活。这种独来独往,来去随缘的云水生涯,既不可能大事弘法,也不方便摄受学人。道信北渡黄梅,建立起了禅宗的殿堂,不再“或岩居穴处,或寄律寺”,(35)而是“择地开居,营宇玄像。(36)存没有迹,旌榜有闻”。(37)公开、普遍地传禅授法,“诸州学道,无远不至”(38)。到他示寂时,山中达五百馀人。(39)弘忍得其传承后,在东山立寺,影响更大,“道俗投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40)以至临终时不无骄傲地说:“吾一生教人无数。”(41)“东山法门”经过两代人的开启和传播,黄梅一时成为了全国禅教的中心。禅宗后来常说:“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宗丛林的创建,似可提早到道信和弘忍的时代。
其次,道信对於禅宗思想和入道方便上,也作出了有益的建设和改革。唐/净觉《楞伽师资记》“唐朝蕲州双峰山道信禅师”说:
其信禅师,再敞禅门。宇内流布有《菩萨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42)
有关《菩萨戒法》的内容,《楞伽师资纪》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联系道信倡导的“一行三昧”禅法,其戒法当属“安心”和“见性”的方便法门,旨在制止修禅过程中妄念的泛起。戒与禅相辅以行,正是“东山法门”的门风之一。菩萨戒属於大乘菩萨所受持的戒律,与小乘声闻所受持的戒律有所不同。达摩以下二传、三传,所修都是头陀行。十二头陀行本属声闻乘律仪,但是达摩从一开始提出“二入四行”时,就已经为其注入大乘思想。尤其是第四“称法行”,(43)强调在“三轮体空”中修行大乘菩萨的六度,自利利他,“庄严菩提之道”,在根本上和菩萨戒的精神是一致的。可见达摩所传禅法,从一开始就为禅宗重视菩萨戒点燃了慧灯。道信开宇后的实际情形,已与十二头陀行不相融合,以菩萨戒法取代头陀行,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又据史载,梁武帝、陈文帝和隋炀帝都曾受过菩萨戒,从者乃至数万人,足见其风气之盛。道信在禅宗的传承上,首倡菩萨戒法,也似存有时代风尚的影响。
这种戒禅结合的门风,也为后来南能北秀所继承。神秀《大乘无生方便门》说:“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瞥起,即违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菩萨戒。”(44)惠能《坛经》曾引《菩萨戒经》说:“戒本源自性清净。”并发挥说:“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45)不过惠能已改念佛为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菩萨戒也改为受无相戒了。(46)
道信还是将“一行三昧”引入禅宗的第一人,“一行三昧”也是东山法门的标志之一。据文献记载,神秀於大足元年(701)被召入东都,“随驾往来,二京教授,躬为帝师。则天大圣皇后问神秀禅师曰:‘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答曰:‘禀蕲州东山法门。\’问:‘依何典诰?’答曰:‘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则天曰:‘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以秀是忍门人,便成口实也。”(47)
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开章明义即说:“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取《楞伽经》印心,乃初祖以来的传承;而“一行三昧”的源流,则取自天台宗的智顗。我们知道,道信曾居止大林寺十年,庐山乃是天台、三论宗的重镇,而天台宗在当时的影响又如日中天,在这种历史和环境的薰陶下,受其影响也不为无因。智顗《摩诃止观》说:“《法华》云:‘又见佛子,修种种行,以求佛道。’行法众多,略言其四:一常坐,二常行,三半行半坐,四非行非坐。”(48)藉此四种修法,即可正观实相,住于三昧。他在进一步阐述“常坐三昧”时说:
一常坐者。《文殊说》(49)、《文殊问》(50)两般若,名为一行三昧。今初明方法,次明劝修。方法者,身论开遮,口论说默,意论止观。身开常坐,遮行住卧。或可处众,独则弥善。居一静室,或空闲地,离诸喧闹。安一绳床,傍无馀座。九十日为一期。结跏正坐,项脊端直。不动不摇,不萎不倚。以坐自誓,肋不至床,况复尸卧,游戏住立。除经行食便利,随一佛方面,端坐正向。时刻相续,无须臾废。所开者专坐,所遮者勿犯。不欺佛,不负心,不诳众生。口说默者,若坐疲极,或疾病所困,或睡盖所覆,内外障侵夺正念,心不能遣却,当专称一佛名字,惭愧忏悔,以命自归,与称十方佛名功德正等。(51)
道信在四种三昧里,只撷取了“一行三昧”亦即“长坐三昧”一种,而且在具体修法上,也不全同智顗所论。他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里详细地论述道:《文殊说般若经》云:“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能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捨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夫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普贤观经》云:“一切业障海,皆从妄相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是名第一忏悔。并除三毒心、攀缘心、觉观心念佛,心心相续,忽然澄寂,更无所缘念。《大品经》云:“无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无所念?即念佛心名无所念。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所以者何?识无形,佛无相貌。若也知此道理,即是心常忆念佛,攀缘不起,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入此位中。忆佛心谢,更不须徵。即看此等心,即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亦名正法,亦名佛性,亦名诸法实性实际法,亦名净土,亦名菩提金刚三昧本觉等,亦名涅槃界般若等。名虽无量,皆同一体,亦无能观所观之意。如是等心,要令清净,常现在前。一切诸缘,不能忓乱。何以故?一切诸事皆是如来一法身故。住是心中,诸结烦恼自然除灭。於一尘中具无量世界,无量世界集一毛头端,於其本事如故,不相妨碍。《华严经》云:“有一卷经卷,在微尘中,见三千大千世界事。”略举安心,不可具尽。其中善巧,出自方寸。(52)
我们拿道信与智顗的说法两相比较,就可以发现:道信取《文殊说般若经》而舍《文殊问般若经》,把克期取证的九十日放宽到一年、三五年,以至更长。(53)四祖身体力行,“昼夜常坐不卧,六十余年,胁不至席。”(54)并且常常以此为教:“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55)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能如此者,久久堪用。如猕猴取栗子中肉吃,坐研取,此人难有。’”(56)五祖弘忍在其门下,也是“昼则混迹驱给,夜则坐摄至晓,未尝懈怠,精至累年”。(57)达摩本有“面壁九年”的传说,“东山法门”更以坐禅作为门风相号召。
道信曾在吉州教导百姓念“般若”退贼,说明他早在江南的时期,就已经奉持摩诃般若波罗蜜了。此际只是轻车熟路,将达摩禅以《楞伽经》印心的传承,与般若系的“一行三昧”,自然融合统一,体现了“东山法门”的又一特色。我们知道,念佛是净土宗的一个重要特征。道信倡导的“一行三昧”的念佛法门,与净土宗虽有渊源,但是又有所区别。
首先,净土宗行者念佛的目的是往生西方,念佛是求生净土的修行方法。净土既在心内,也在十万亿佛土之外。而道信提倡念佛,只是为了直探心源,自证菩提,将念佛当作引发禅定的特有方便。他认为即心即佛,无须外求:
问:“临时作若为观行?”信曰:“直须任运。”又曰:“用向西方不?”信曰:“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即是净佛国土,更不须向西方。……佛为钝根众生,令向西方,不为利根人说也。”(58)
道信的净佛国土自在於心,后世称作“唯心净土”。很明显,他对西方净土说虽不否定,但对於这种行者却至为轻视。
其次,净土宗在其始,对於实相念佛、观想念佛和称名念佛三种念佛法门,都无所偏废,而着重於观想念佛。后来因为重点移向了《阿弥陀经》,也就专以阿弥陀佛为念了。被推为中国净土宗二祖的善导(613-681)在《观无量寿经疏》“观经玄义分卷第一”说:“今此《观经》中十声称佛,即有十愿十行具足。云何具足?言‘南无\’者,即是归命,亦是发愿回向之义。言‘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以斯义故,必得往生。”(59)而道信所主张的“系心一佛”,只是心惟,而非口诵。也无专定的对象,甚至认为,一即一切,念一佛“亦与念无量诸佛功德无二”。
第三,净土宗念佛,乃是企望取得阿弥陀佛的愿力作增上缘,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正如北魏/昙鸾所说:“易行道者,谓但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乘佛愿力,便得往生彼清净土。”(60)而斥“唯是自力,无他力持”的求阿毗跋致(不退转)为难行道。道信主张的念佛,只被当作抑制外缘以定开慧的手b段。他说:“常忆念佛,攀缘不起,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61)
第四,初期净土宗在念佛时往往须要观想佛的相好功德。即如善导,他既以称名念佛为正行正定业,又著《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教人结跏趺坐后,“即以心眼,先从佛顶上螺髻观之”,依次为头、脑以至胫、足。(62)道信主张的念佛,则只“专称名字”,“不取相貌”,“直须任运”,无须观行。
道信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在论及了“一行三昧”即念佛三昧,念佛是自证菩提的方便法门之后,又有下面一段释惑的文字:
问:“云何能得悟解法相,心得明净?“信曰:“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心,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自运。亦不令去,亦不令往,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心如明镜。或可一年心更明净,或可三五年心更明净。或可因人为说即悟解,或可永不须说得解。经道:众生心性,譬如宝珠没水,水浊珠隐,水清珠显。为谤三宝、破和合僧诸见烦恼所污,贪、嗔颠倒所染,众生不悟心性本来常清净,故为学者取悟不同,有如此差别。今略出根缘不同,为人师者善须识别。”(63)
就是说,上面所说的安心方便,也未可一概而论。由於人的根机的不同,“心得明净,悟解法相”,也可以不藉助念佛看心等,自然获得。“为人师者善须识别”,方能作到因人施教。他最后的结论很灵活:“略举安心,不可具尽,其中善巧,出自方寸。”自证如何,就看各人的因缘、根机和解行的程度了。这为后来南禅的无所执着,随心任运,种下了方便的种子。
东山寺和“东山法门”的正式建立,最终还是完成在弘忍的手里。不过,没有道信的北渡黄梅,禅灯就不可能历史地传给弘忍。但是,弘忍的青出於蓝,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实。《传法宝纪》说:“道俗投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64)“乃莫之过”当然也包括了道信。
弘忍(601-6074),俗姓周,黄梅人。童真出家,十二岁事道信。(65)“缄口於是非之场,融心於色空之境”。(66)《历代法宝记》说他:“常勤作务,以礼下人。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常懈倦。三十年不离信大师左右。”(67)道信临终,问谁可承传,道信说:“弘忍差可耳。”(68)唐高宗咸亨五年(674)示寂,春秋七十四。(69)
弘忍同其列祖一样,没有自撰过著作,其《修心要论》(70),也题名“导凡趣圣悟解脱宗”或“蕲州忍和上导凡趣圣悟解脱宗修心要论”,(71)是弟子们撮其大旨笔记而成,并非弘忍亲自拟定。《楞伽师资记》说:“其忍大师,萧然净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在人间有禅法一本,云是忍禅师说者,谬言也。”(72)近人研究发现,《修心要论》同《楞伽师资记》里慧可所说法甚为相似。由此推断,弘忍不但传有本禅法,而且是上承着二祖。(73)但是,净觉是弘忍的弟子,不可能对於禅宗传灯不了然於心,即使本书不是弘忍而为慧可所说,也决不至斥为“谬言”。因此,净觉所指可能非是《修心要论》。
弘忍的基本禅学思想仍是秉承道信,但是有所深化和拓展。他认为:一切众生本具清净之心,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进而提出他的“守心”论,认为是达到自证菩提、解脱成佛的根本法门。《修心要论》一再地强调这一点:
一切众生迷于真圣,不识本心,种种妄缘,不修正念。不正念故,即憎爱心起。以憎爱故,即心器破漏。心破漏故,即受生死。有生死故,即诸苦自现。《心王经》云:真如佛性没在知见六识海中,沉沦生死,不得解脱。努力会是,守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灭,故自然与佛平等。(74)
又说:
既体知众生佛性本来清净,如云底日,但了然守真心,妄念云尽,惠日即现。(75)
道信只提在一切行住坐卧中,观其清净本性;而守住本净之心,不让妄念污染,提出修心的要求,则是弘忍禅学思想的发展。后来的北宗,就在“不使惹尘埃”一点上,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弘忍还说:
夫修道之体,自识当身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见(76)本师,胜念十方诸佛。(77)
又说:
欲知法要,守心第一。此守心,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78)
弘忍虽说没有说放弃念佛,至少是置於了不太重要的位置。又像如此将心性驾凌乎三世诸佛和十二部经之上,也为前此宗师言论中所不曾见。这与南宗后来专重心解,而将教门其余弃而不顾,当然有着直接的关系。
弘忍在对待念佛这一问题上无疑是继承了道信的思想的。(79)此时的黄梅,已经“十馀年间,道俗投学者,天下十八九。”(80)这么多的人,如何教化?在运用念佛这个修行方式上,与道信又有何同异?《传法宝纪》为我们透露了一些消息:
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密来自呈,当理与法,犹递为秘重,曾不昌言。倘非其人,莫窥其奥。至乎今之学者,将为委巷之谈,不知为知,未得谓得,念佛净心之方便,混此彼流。真如法身之端倪,曾何仿佛。悲夫,岂悟念性本空,焉有念处?净性已寂,夫何净心。念净都亡,自然满照。於戏,僧可有言曰:“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信矣。(81)
但是,究竟是怎么一个念佛法,《传法宝纪》语焉未详。《修心要论》在这个方面作了详细的介绍:
若初心学坐禅者,依《无量寿观经》端坐正身,闭目合口,心前平视,随意近远,作一日想,守之,(82)念念不住。即善调气息,莫使乍粗乍细,即令人成病苦。若夜坐时,或见一切善恶境界,或入青黄赤白等诸三昧,或见自身出入光明,或见如来身相,或见种种变现,知时摄心莫著,皆并是空,妄想而现。经云:十方国土皆如虚空,三界虚幻唯是一心作。若不得定,不见一切境界者,亦不须怪。但于行住坐卧中,恒常了然守真心,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即灭。一切万法不出自心,所以诸佛广说若许多言教譬喻者,只为众生行行不同,遂使教门差别。其实八万四千法门,三乘位体,七十二贤圣行宗,莫过自心是本。(83)
可见,东山门下的念佛,至此时已经不完全采用道信的念佛名的办法,而是赋予了很强的“观念”色彩。即依据《观无量寿经》所述之“十六观”法,(84)以为入定之方便,其中“若不得定,不见一切境界者,亦不须怪”一语可证。“作一日想,守之”,修的正是“十六观”中的日观(也叫日想观),即观日落,正坐向西,忆想西方,令心坚住,观日没状如悬鼓,闭目、开目皆令明了。(85)这样长时间地修下去,直到“但于行住坐卧中,恒常了然守真心,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即灭”,了悟“一切万法不出自心”之时,“即自见佛性”。这个时候,就该如《传法宝纪》所说,“密来自呈,当理与法”了。
然而,弘忍对念佛求生西方始终是否定的,他甚至说念他佛不免生死,守我心才能得到彼岸:
问曰:“云何凡心得胜佛心?”答曰:“常念他佛,不勉生死。守我本心,得到彼岸。故《金刚般若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故知守真心胜念他佛。又言胜者,只是约行劝人之语,其实究竟果体,平等无二。”(86)
这样,就从根本上同净土宗的念佛划清了界限。当然,念佛不能了生死,只是宗门见解,多少带有自高门户的意味,并非符合经典的了义。但是,弘忍是从方法论而不是从本体论上否定念佛的。他所否定的,其实是借助他力向心性之外别求往生这种修行方式,对念佛往生最后成就的佛果与守心最后成就得佛果,他不认为孰高孰低。但是,念佛名下手尚易,观念成就甚难,而通过念佛达到净心(守心)则难上加难。净心后“密来自呈,当理与法”,在弘忍门下乃“秘重”之事,“倘非其人,莫窥其奥”。大家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念佛,而难知念佛后的印心。未能登堂入室者自然有种种的揣测,也难怪《传法宝纪》中感叹“至乎今之学者,将为委巷之谈,不知为知,未得谓得,念佛净心之方便,混此彼流”了!
南能北秀
弘忍的弟子众多,出类拔萃的也不在少数。其中最著者有十弟子,而惠能、神秀又是十弟子中的翘楚。因为他们两个后来各在一方传法,禅法上又有着渐、顿的分歧,被当作南顿北渐的代表。

神秀(?-706),俗姓李。汴州尉氏人。(87)年四十八,从忍禅师所受得禅法。“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88)与禅宗历代祖师的宗风一脉相承。据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说,弘忍曾经赞叹:“东山之法,尽在秀矣!”(89)武则天久视元年(700),迎请神秀入京,备极尊崇。神龙二年,灭度於洛阳,大概活了上百岁。(90)归葬当阳玉泉寺,赐谥“大通禅师”。
张说在《大通禅师碑铭》中,说到神秀的禅法:“持奉《楞伽》,近为心要。”(91)《楞伽师资记》和《传法宝记》,都只收有神秀传,而不及惠能。朝庭推他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92)。世人尊之为“得道果”、“不可思议人”(93)。说明当时的朝野上下,都是把神秀视作禅宗的嫡传(94)。而神秀对於师承由来,也未敢或忘,据《楞伽师资记》载:“则天大圣皇后问神秀禅师曰:‘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答曰:‘禀蕲州东山法门。\’问:‘依何典诰?’答曰:‘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95)
我们注意到,神秀的作答与道信的禅法有了不同,只提《文殊说般若经》,而未提《楞伽经》。(96)这也给了我们一个信息,此时的东山门下,已经不太以《楞伽经》为重,而逐渐地将目光移向了《大乘起信论》。这或许也是整个北宗理念变化的反映,因为杜朏的《传法宝纪》序和净觉的《楞伽师资记》序,都是先引《大乘起信论》为据,《楞伽经》已经退居其次或竟只字不提。但是我们不能以此而说神秀放弃了《楞伽经》,他所倡的渐修之法,便是来自《楞伽经》;也是来自达摩及东山法门,所以张说才说“递为心要”。四卷《楞伽经》说:
尔时大慧菩萨,为净自心现流故,复请如来白佛言:“世尊,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为顿为渐耶?”佛告大慧:“渐净非顿,如庵罗果渐熟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譬如陶家造作诸器。渐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譬如大地渐生万物非顿生也;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97)
由此可见,后来南宗攻击北宗“师承是旁,法门是渐”(98)的说法,并非的论。是渐不假,是旁则非。
神秀继承了禅宗历来的作风,不立文字。敦煌本《观心论》、《大乘无生方便门》等书,据研究,不是神秀所著,为其弟子所记或所撰。《观心论》的主旨,在对心性和成佛的认识上,没有脱出道信“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以及弘忍《修心要论》的见解,只是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心是众圣之源,心为万恶之主。”“常乐由自心生,三界轮回亦从心起。”“心为出世之门户,心是解脱之关津”(99)。所以,观心、守心、净心乃“总摄诸行”,“若能了心,万行俱备”。并且,他将道信纯为禅定的念佛观,与修善断恶联系起来,作为修禅的一个有机部份:
夫念佛者,当须正念为正,不了义即为邪。正念必得往生净国,邪念云何达彼?佛者觉也。所为觉察心源,勿令起恶。念者忆也,谓坚持戒行,不忘精勤,了如来义,名为正念。故知念在于心,不在言也。因筌求鱼,得鱼妄(100)筌;因言求言,(101)得意忘言。既称念佛,云何须行念佛之体。若心无实,口诵空名,徒念虚功,有何成益?且如诵之与念,名义悬殊,在口曰诵,在心曰念。故知念从心起,名为觉行之门;诵在口中,即是音声之相。执相求福,终无是乎。故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102)
如前所论,神秀以修善断恶为内容的念佛观,是在弘忍《修心要论》基础上发展、深化而来。
《传法宝纪》说:“及忍、如、大通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103)有关神秀的念佛情况,《大乘无生方便门》有着如此的记载:
各各胡跪合掌,当教令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证。次请十方诸佛为和尚等,次请三世诸佛菩萨等,次教受三归,次问五能:一者汝从今日乃至菩提,能舍一切恶知识不?能。二者亲近善知识不?能。三能坐持禁戒乃至命终,不犯戒不?能。四能读诵大乘经问甚深义不?能。五能见苦众生随力能救护不?能次各称已名忏悔罪言过去未来及现在身口意业十恶罪:我今至心尽忏悔,愿罪除灭永不起五逆罪障重罪。准前。譬如明珠没浊水中,以珠力故水即澄。清佛性威德亦复如是,烦恼浊水皆得清净。汝等忏悔竟,三业清净,如净琉璃内外明彻,堪受净戒。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瞥起,即违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持菩萨戒。三说。次各令结跏趺坐,同(104):佛子,心湛然不动是没?言:净。佛子,诸佛如来有入道大方便,一念净心,顿超佛地。和(105)击木,一时念佛。(106)
神秀采用的仍然是念佛净心的方法。从所提供的情节看,弘忍以及后来的北宗,修禅的各个环节大都已经程式化了,这也许是门人上了千百之后,不得不如此的原故。道信的时代可能已见端倪,或许尚不至如此之完善。《观心论》所述明确告知:禅宗奉行的念佛,是指在心忆念,并非口出音声。以有实体的“念”,还是无实体的“诵”,区分为正念或邪念。“既称念佛之名,须行念佛之体。若念无实体,口诵空名,徒自虚功,有何成益?”不以净土宗的称名念佛为然,与道信诸祖的思想一脉相承。但是,神秀将向外求佛转变为观心自照,与道信所称的念佛,在认识和实践上又有了差异。
神秀虽说也有“顿超佛地”之论,但在方法上主要还是取“时时勤拂拭”的阶渐修禅方式,更多的继承了“东山法门”的禅法。他在《大乘无生方便门》里提出五方便门:“第一总彰佛体,第二开智慧门,第三显示不思议法,第四明诸法正性,第五自然无碍解脱道。”(107)会通了《大乘起信论》、《法华经》、《维摩诘经》、《思益梵天经》和《华严经》等佛教经论,其修证内容之广、之繁,又为道信、弘忍所不及。总之,神秀的禅法,比之不假方便、单刀直入的南宗来,显得过多执著於修持过程中的种种方便了。
惠能(638-713),俗姓卢,新州人。(108)“父早亡,母亲在孤。艰辛贫乏,能市卖柴供给”(109)。得悉五祖持《金刚经》诲人,“即得见性,直了成佛”,即辞亲往黄梅。(110)初礼忍大师时,就作出了“身虽是獠,佛性岂异和上?”(111)的非凡回答。他在寺中随众踏碓,并随大众“默然受教”。(112)弘忍临示寂时,曾说:“如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後传吾道者,只可十耳。”惠能列在其中,并称许他“堪为人师”。(113)得五祖秘传衣、法后,潜回南方多年,方在法性寺出家,随往曹溪公开传法。朝庭曾多次派人征召,均以病辞不赴。先天元年示寂,春秋七十六。
惠能乃是整个禅宗史上最有作为的人物,他的基本禅学思想,虽说仍不出历代宗师的“见性成佛”之说,但是无论是在理念和方法上,都大有创见和革新。他的禅法思想,主要集中在《六祖坛经》,(114)并被当作历代传承的依据。(115)尽管也是出自弟子的记录,而非惠能亲著。
首先,惠能旗帜鲜明地提倡“顿悟”,与北宗的“渐悟”划分楚汉。一切大乘法门都认为,真如法性乃是顿悟。因此,南北两派在理入方面并不存有分歧,分歧乃表现在行入的一方面。行入是指从初发心到证悟成佛的过程,是历阶渐进还是直接证入,前者为渐,后者则为顿。在《坛经》中,表现其“即得见性,直了成佛”的顿悟思想,可说随处可见:
善知识,即烦恼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116)
又如:
汝若不得自悟,当起般若观照,刹那间,妄念俱灭,即是自真正善知识,一悟即至佛地。(117)
再如: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118)
所谓“前念、后念”、“刹那间”、“顿见”,便是顿悟在时间上的体现。《坛经》里还讲了一个志诚奉神秀之命,到曹溪秘密探听情况的故事。末了说:“志诚闻法,言下便悟。”(119)证明南顿的禅法,要比北渐高明得多。但是,惠能又特别指明,顿、渐乃是人的见迟见速的反映,而不是说法也有渐和顿之分别:“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渐顿?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渐顿。”(120)佛教历来认为是“因戒生定,因定发慧”,二者存在有因果和时间的差异。惠能认为: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慧定别。定慧体不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善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定慧各别。(121)
所谓定慧等而无别,也就泯灭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而与其顿悟的理念协调一致。
在《六祖坛经》中,惠能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禅学思想,他在文章中已经对方方面面作了详尽的说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思想的确与《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简称《金刚经》)的义理相一致,旨在阐明法空无我,破除一切虚妄执着,认识宇宙万有的实相。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为本。何名为相无相?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善知识,外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以无相为体。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生念。若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学道者用心,莫不识法意。自错尚可,更劝他人迷,不自见迷,又谤经法。是以立无念为宗,即缘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然此教门立无念为宗,世人离境,不起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维摩经》云:外能善分别诸法相,内于第一义而不动。(122)
又说:
今既如是,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缘境触,触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维摩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123)
惠能说“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不执着於任何的事物或名相,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系缚。因此,他对於一切的成规,都得用他的眼光和思想,进行了审视和评判。故而对於什么叫定,什么叫禅,何为坐禅,都作出自己新的解释。
弘忍提出修心,神秀提出观心,而惠能却认为,心性本净,“看即是妄”,虽说是针对神秀,却也不自觉地将弘忍扫了一下:
善诸识,此法门中坐禅原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言不动。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净,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不见自性本净,心起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却是妄也。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若修不动者,不见一切人过患,是性不动。迷人自身不动,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124)
我们知道,四祖道信是将“一行三昧”引进禅法的第一人,他特别地强调坐的意义:“努力勤坐,坐为根本”。坐禅在弘忍的时代,可谓发挥到了极致。惠能虽说有时也劝人端坐,但基本立场却是相反。
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住即被缚。若坐不动,是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净,不动不起,从此致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倒。即有数百般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错。(125)
何谓“一行三昧”,道信解释为长坐念佛三昧,东山法门即以此为门风。在惠能看来,禅不一定须坐,甚至对拘束於坐的禅者进行了批判。种种表现说明,在六祖的眼里,目的便是一切,不拘於任何形式。后来五家七宗接引方式的百花齐放,就是与此具同一思想根源。
《坛经》全书的主旨,就在惠能於大梵寺讲升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126)他解释说:“何名摩诃?摩诃者是大。”“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惠。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惠,即名般若行。”“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梵音,言到彼岸。”(127)简言之,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获得解脱的佛慧。惠能屡屡赞颂般若,并且还与《金刚经》联系起来:
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128)
又说:
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129)
再如: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须修般若波罗蜜行。但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当知此人功德无量。经中分明赞叹,不能具说。此是最上乘法,为大智上根人说。小根智人若闻法,心不生信。(130)
一些治禅宗史的人,看到惠能阐述“本源空寂”和对於般若妙智的重视,便认为:自达摩以至弘忍,都是用《楞伽经》印心;到了惠能时代,改弦更张,采用了《金刚经》印心。其实,惠能的传承仍是源自东山法门。据文献载,道信即曾教吉州百姓念“般若”以退贼,惠能所受《金刚经》也出於弘忍的秘传。(131)相反,又有的学者认为:禅宗用《楞伽经》或《金刚经》印心,都是一种“宗教传说”(132),完全否定《楞伽师资记》、《坛经》的记载。我们以为,忽视历史或者现实,都是一种片面性。
我们前面论到,北宗神秀在习禅时,尚犹保存了念佛的法门。可是在惠能的殿堂上,就只能听到“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密”的声音了。《坛经》里记载惠能答韦使君的一段关於念佛的问题:
使君礼拜。又问:弟子见僧俗常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望为破疑。大师言:使君,听惠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国,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只为下根说远,说近只缘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使君,东方但净心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迷人愿生东方。两者所在处,并皆一种心地。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除十恶即行十万,无八邪即过八千。但行直心,到如禅指。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133)
又说:
照三毒若除,地狱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134)
再如:
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135)
惠能对於西方净土的看法,同道信的观点(136)和弘忍的观点(137)可谓完全一致,只是道信与弘忍尚以念佛为方便,这时,惠能不仅不用此方便,而且作了更彻底的否定。《坛经》的韦使君何以有念佛得往生西方一问,当然不是偶然的。联系当时的历史,我们以为,惠能的以上这番话,可能还是有为而发。
与惠能同时代的净土宗大师是善导。他继昙鸾、道绰之后,集净土学说和行仪之大成,并使之风行天下,人称“弥陀化身”。(138)善导建立的“凡夫为本说”、“往生报土说”、“持名具足说”、“定散二善说”、“往生正因说”、“仪轨辅助说”,使得净土宗理论得以完备。善导在唐代的巨大影响,如宋/志磐《佛祖统纪》卷第三十九“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六”记载:
十五年。善导法师至西河见绰禅师九品道场,讲诵《观经》。喜曰:此入佛之津要也。修余行业迂阔难成,唯此观门速超生死。至京师击发四部三十余年,般舟行道。造《弥陀经》十万余卷,画净土变相三百余壁。满长安中并从其化,有终身诵《弥陀经》十万至三五十万卷、日课佛名一万至十万声者。师念佛时有光明从口出,后高宗朝,赐寺名曰‘光明\’云。(139)
善导到长安是在道绰去世后,即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善导此时33岁,而惠能尚是少年。等到惠能在广州法性寺受戒、(140)入曹溪山宝林寺时,(141)善导已在长安教化三十馀年,“满长安中并从其化”,早已名满天下了。在善导的思想里,往生正是最根本的目的,持名念佛是达成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方法。所以他说:
三明增上缘。众生称念即除多劫罪,命欲终时,佛与圣众自来迎接,诸邪业系无能碍者,故名增上缘也。自余众行,虽名是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校也。是故诸经中处处广赞念佛功能,如《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唯明专念弥陀名号得生。又如《弥陀经》中,一日七日专念弥陀名号得生,又十方恒沙诸佛证诚不虚也。又此经定散文中,唯标专念名号得生。此例非一也。(142)
对于观想念佛,他虽然承认为佛亲说,但认为非佛本愿。善导解释原因说:
如《文殊般若》云,明一行三昧,唯劝独处空闲,舍诸乱意,系心一佛,不观相貌,专称名字。即于念中,得见彼阿弥陀佛及一切佛等。问曰:何故不令作观,直遣专称名字者,有何意也?答曰:乃由众生障重,境细心粗,识扬神飞,观难成就也。是以大圣悲怜,直劝专称名字,正由称名易故,相续即生。(143)
那么,即使要求往生,十方佛国均可,为什么一定偏指西方?善导说:
诸佛所证平等是一,若以愿行来收,非无因缘。然弥陀世尊本发深重誓愿,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但使信心求念,上尽一形,下至十声一声等,以佛愿力,易得往生。是故释迦及以诸佛劝向西方。(144)
善导为净土宗大敞门户,不仅女人、根缺者(黄门)可以往生,“一切善恶凡夫可入”,乃至五逆谤法俱得往生。善导使净土宗完全成为普通人的归宿,而与专“为大智上根人说”(145)的“自悟自修”(146)法门大相径庭。无怪乎惠能关於净土问题的观点带有“针对”的痕迹。
不过,惠能对於净土宗的批评,却不无可以检讨的地方。明代莲池袾宏在《正讹集》“西方十万八千”中指出:
《坛经》以十恶八邪譬十万八千,人遂谓西方极乐世界去此十万八千,此讹也。十万八千者,五天竺国之西方也。极乐去此盖十万亿佛刹。夫大千世界为一佛刹,十万亿刹非人力所到,非鬼力、神力、天力所到,惟是念佛人一心不乱,感应道交,到如弹指耳,岂震旦诣乎天竺,同为南赡部之程途耶?
将十万亿佛国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说成离我们十万八千里远,确然是将两个“西方”(西方净土与西天印度)混为一谈。对此,莲池进而解释说:
然则六祖不知西方欤?曰:《坛经》是大众记录,非出祖笔。如六经四子,亦多汉儒附会,胡可尽信。不然,举近况远,理亦无碍。如在市心,以北郊喻燕京,以南郊喻白下,则借近之五天,喻远之极乐,欲时人易晓耳,何碍之有。(147)
莲池的话,可谓面面俱到。首先,肯定这个说法错了,但错不在六祖,而在记录者。可是,万一这确实是六祖所说,又怎么办?於是他又回护说,那是一个比喻。这个问题还可以比喻化解,“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这句话的“杀伤力”就太大了,简直要动摇净土宗赖以存在的根本。莲池本身是参禅开悟的人,但却又竭力提倡净土,对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实在不能回避。所以莲池又在《竹窗三笔》之“六祖坛经”为之辩护说:六祖示不识字,一生靡事笔研,《坛经》皆他人记录,故多讹误。其十万八千东方西方等说,久已辩明。中又云:但修十善,何须更愿往生。夫十善,生天之因也。无佛出世,轮王乃以十善化度众生。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见佛,而但生天,可乎?其不足信明矣。故执《坛经》而非净土者,谬之甚也。(148)
六祖当然是不会错的,错的自然是《坛经》。而《坛经》如果全是六祖亲说,那六祖不还是错了?这样,板子只好打到记录人的身上。其实,莲池的不能说又不能不说的矛盾,有其不得已的成分在里面,这与六祖的成就与影响有关。但是,莲池敢于指责《坛经》,这需要的不仅是巨大的勇气,更需要自身的道德、行持、见地、学问、事功作为支撑点。作为“法门之周孔”(149)的莲池,无疑是有资格的,以至于此后无人对他的指责提出异议。
然而,这段问答,当然不是记录错了,其思想与《坛经》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如《坛经》说:
凡夫不解,从日至日,受三归依戒。若言归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即无所归。既无所归,言却是妄。(150)
佛既不须外求,念佛的作用也就可见了。南宗彻底地否认念佛,虽是道信“亦不念佛,……直任运”思想的扩大和深化,实质却有些不同:道信是说无须如此,即可以得证菩提,这是就上根人说的;而惠能却是彻底的否定有此必要了。惠能论点的核心,即在於自性、自力、自悟。其实,在佛法修学中,并没有完全绝对的自力或者他力。“自”与“他”始终是鸟之二翼、车之双轮,片面强调一点而否定另一点,都是不利于佛法的弘传的。宋以后出现的“禅净融合”的观点,未尝不是一种深刻的反思和检讨。
况且,从净土宗的观点来看,《坛经》的这段话,很有讨论的必要:比如,《坛经》说:“东方但净心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可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151)所谓“阿鞞跋致”指在佛道修行的过程中,不退失既得的功德。小乘有部以预流果为不退,大乘则以初住、初地、八地等为不退。明/智旭《阿弥陀经要解》指出,念佛往生者有“四不退”,即一念不退,二行不退,三位不退,四毕竟不退。(152)既不退,又怎么会出现“西方人心不净”的情况呢?另本《坛经》甚至出现“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的话来,(153)更是匪夷所思。如果西方人(指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还会造罪,那么西方也就不是净土了。再如“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等话,如果能够成立,那《观无量寿经》中说的那些造五逆十恶罪、“以诸恶业而自庄严”(154)的罪人,根本就没有往生希望,而净土法门也不会被称为“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了!
《坛经》到底是错解净土典籍还是曲解净土典籍,我们无从判断,但是《坛经》的话终于成为禅宗行者否定净土宗的口实。而这一影响,从唐至清,始终难以消除,哪怕是禅宗或净土宗的大德一再调和,也无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