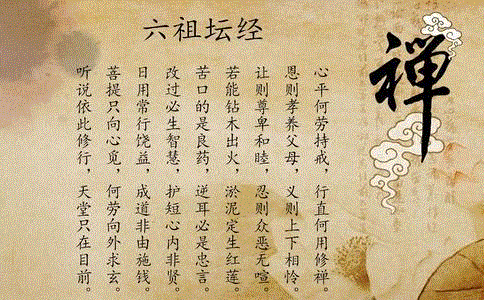太上感应篇图说92:减人自益
发布时间:2024-08-21 03:04:47作者:六祖坛经全文网
经文:减人自益。
【原文】
兄弟如同鸟共林,独吞家产是何心。
遗容轴内藏遗嘱,巧宦从中得万金。
注:减损他人,自取饶益,只愿己富,不管人穷,究竟天道恶盈,一时虽讨便宜,不失于此,必失于彼,不失于目前,必失于日后,不失于其身,必失于其子孙,平心定气,冷眼静观,百无一谬也。
案:闽中富宦倪某,年七十娶妾生一子,名真郎,已十岁。倪老病,妾左右侍奉,乘间言曰:“主翁倘有不讳,此茕茕者,将何所托?”倪曰:“我为此事筹之熟矣,长子为人好占便宜,我死一应产业,势必全吞。真郎幼孩,若与相争,是以羊敌虎,万无生理。我有小照一轴,尔可慎藏,俟真郎成人,遇明白官府,持以控告,管尔母子受用不尽。”言讫,即呼长子至榻前,写遗嘱,将业全判执管,妾母子拨给东园草房五间,日与米二升、钱十文为养赡。须臾目瞑,长子不候七终,将妾母子驱入草房,遗命钱米十不给二。妾与人缝裳,苦捱度日。真郎年已十六,时逢除夕,长子宅内备极繁华,妾母子孤灯相对,灶冷厨荒,凄凉无限。真郎曰:“儿非父之子乎?产业理应均分,今兄富儿贫,母并不敢言,何也?”妾曰:“尔父在日已虑及此,与我画一轴,命俟尔成立之日,持画控告,定有好处。尔年已十六,又新任秦县主断事极明,我与尔合当往控。”遂于开印日母子呈画哭诉,秦公展看,乃一年老官员怀抱幼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不得其解,吩咐异日候审。退堂细思曰:“怀抱幼子,乃此子系伊亲生也。一手指天,欲问官照天理断也,一手指地,不知何谓?”乃取画向日照之,见内隐隐有一指阔寸余长纸折在内。忖曰:“是必有异。”轻轻挑开裱纸,取出看明,大喜。次日,乘轿至倪宅亲勘,长子出接。公曰:“尔弟告尔独占家产,有之乎?”长子出遗嘱为据。公曰:“俟到草屋看明,当有公断。”方至屋,忽作揖逊状曰:“原来是倪老先生。”坐定,又作听语状曰:“大公郎如此欺心,即当重究。”稍停,又曰:“既老先生为大郎说情,但二郎何以存活?”又停半晌曰:“老先生可谓深心矣,如此厚赠,断不敢当,大驾请回,即当处分”。又作送客状,至门外三辑而回。遂设公案,排衙升座。喝大郎跪下,责之曰:“妻有大小,子无嫡庶,尔何敢独据父产?适间我所见穿绿袍、白须、面有点痣者,非尔父耶?”大郎叩首称是。公曰:“令尊不忍尔受刑法,再四求饶,只尔弟母子何以安插?”大郎曰:“父有遗言,日给米二升、钱十文矣。”公曰:“并此亦不用破费,遗嘱产业照旧与尔享用,只此草房之内,上至天下至地,一切所有俱归尔弟。”大郎思家业全得,又日省钱米,数间空屋落得应承,遂亲写遵依。公即命人挖开东首地土,有白银万两,曰:“此尔父分与尔弟者。”挖西边地土,曰:“此下有几两黄金,系尔父送我作谢者。”挖一巨坛,内藏黄金千余。公立命抬回,断银与妾母子,立案永不许再争。秦公可谓巧于取财者矣。
附:将乐县之万安寨有张孝廉某,贪而放,颇侵剥乡邻以自益,人不敢忤。家本贫,后遂骤富,临溪筑室连楹,曲水方亭,雕栏复磴,结构甚侈。亡何,谒选得蜀中县令,道病卒,家随以破。今其屋室归予乡人夏生,而孝廉一子,反依栖执役,略不知愧。予丁酉,过夏生家,见奄奄一息,零落琐尾之状,心感之。因坐方亭,作诗曰:“九曲池塘活水流,雕栏面面俯清幽。半生心力经营尽,好与人间话鹊鸠。”盖为之纪其实云。(《悬榻编》)
江州朱原虚,有诗名,父亡时,二弟幼,原虚匿父所遗绫锦十余箧。二弟流离居外,原虚乡试,屡不售。偶请乩,仙降笔曰:“何处西风夜卷霜,雁行中断各悲凉。吴绫越锦藏私箧,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虚得诗,惶恐召二弟归,均分,劝勉力学。后俱登弟。(《桂香境》)
薛包与诸弟,分财异居,田庐取荒顿者,曰:“吾少时所理也。”奴婢取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尔等不能用也。”器物取其朽败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后诸弟皆破产,而包复赈之。(《感应篇集注》下同)
林退斋临终,子孙跪膝前,请曰:“大人何以训儿辈?”退斋曰:“无他言,只要汝曹学吃亏。从古英雄只为不能吃亏,害了多少事。”
【译文】
注:削减损害他人,自己得到丰饶的利益,只希望自己富贵,不顾别人的贫穷。毕竟天道厌恶盈满,一时间虽然讨得了利益,没有在这里失去,一定会在那里失去,不在眼前失去,一定在日后失去,不在自己身上失去,一定在子孙后代身上失去。心平气和,用冷峻的眼光观察,许多事都符合这个道理。
案:福建有个富甲一方的官宦倪某,年纪七十岁,娶了一个妾,生下一个儿子,名字叫真郎,已经十岁了。倪某年纪大了,生了病,小妾在左右服侍,乘机说道:“老爷如果有什么不测,这孤孤单单的儿子,将如何寄托?”倪某说道:“我为这事早已筹划成熟了,大儿子做人喜欢占便宜,我死后所有的产业,从情势上看他一定要全部占有,真郎这孩子年龄小,如果与他相争斗,真是羊与老虎相斗,一点也没有获得生存的理由。我存有一幅小像,你可以小心收藏起来,等到真郎长大成人,碰到聪明清白的官吏,拿上这幅小像去告官,保管你母子二人平生享用不完。”倪某说完话,就把长子叫到床前,当面写下遗言,把家业全部交付长子掌握,小妾母子,分给东边院子的五间草房,每天分给二升米、十文钱,做为奉养的费用。顷刻间,倪某咽了气。长子不等到倪某死后七七终了,将小妾母子赶到草房内居住,倪某遗嘱的钱和米十分不能给二。小妾给人缝补衣裳,苦苦支撑着过日子

真郎年龄已经十六岁了,当时恰逢除夕,长子的房屋内财物完备,极为繁华。小妾母子与孤单的灯火而对,灶上冰冷,厨房荒凉,无比凄冷。真郎说道:“儿子不是父亲的儿子吗?财产家业按理应当平均分配,今天长子富有,儿子贫穷,母亲并不敢说出,为什么呢?”小妾说道:“你父亲在世上时已考虑到这件事,给了我一轴画像,遗命等你成人之时,拿着画到官府控告,一定会有好处。你年纪已经十六岁,并且新上任的秦县令处理事情极为分明,我和你应当去官府控告。”
于是,在审理案件的那天,母子递上画像,哭着诉说经过。秦县令展开画像,看见一位年纪大的官员怀里抱着小孩子,一只手指着天,一只手指着地,他不能够理解,告诉母子二人改日听侯审理。秦令退下公堂后细细想道:怀里抱着小儿子,这是因为这个儿子也是他亲生的。一只手指着天,是想让官府依照天理明断这件事。一只手指着地,不知是什么意思?取出画像对着日光照看,见里边隐约有张手纸宽一寸长的纸条,折叠在里边,他想道:“这一定有奇特的含义。”他轻轻挑开裱贴在画像上的纸,取出来看清,特别高兴。第二天,秦令坐着轿子到倪家亲自查看长子从家里出来迎接,秦令说道:“你弟弟控告你独自侵占家中产业,有这件事吗?”长子拿出倪某遗嘱做为依据。秦令说道:“等到草屋里看明白了,应当有个公平的处理。”刚进草屋,秦令忽然做出拜揖的样子说道:“原来是倪老先生。”坐下后,又做出听人说话的样子说道:“大儿子这样欺骗良心,就应当严加追究。”过一会,秦令又说道:“既然倪老先生为大儿子说情份,但是二儿子怎么生活?”又过了半会儿,秦令说道:“倪老先生可以说是用心深刻。这样丰厚的馈赠断断不敢接受,你的尊驾请回去,随即应当进行处理。”秦令又作出送客的样子,到门外边作了三个揖礼,才返回来。于是,秦令设立公堂,安排衙役,当场升堂问案,喝令大儿子跪下责备他道:“老婆有大小之分,儿子没有亲生后生,你为什么敢于独占父亲的遗产?刚才我所看见的身穿绿色长袍,长着白胡子、脸上有一点痣的,莫非是你父亲吗?”大儿子叩着头说是。秦令说道:“你父亲不忍心你受到刑法处理,多次请求饶恕你,但是你弟弟母子又用什么安排呢?”大儿子说道:“我父亲有遗言,每天给他们二升米、十文钱。”秦令说道:“连这也不用你花费了,你父亲留下遗嘱,家中产业仍然让给你享受使用,只有这草房里边,上到天上下到地下,一切所有的财物都属于你的弟弟。”大儿子想到,家产全部得到,况且每天也省下钱和米,几间空空的草屋,也应当答应下来,于是,亲自写字遵照依从。秦令立即命令手下挖开东边的土地,地里边有万两白银,说道:“这是你父亲分给你弟弟的。”挖开西边的土地,说道:“这下边有点黄金,是你父亲送给答谢我的。”挖开一只巨大的坛子,里边藏着一千多两黄金。秦令立即命令抬回县府,将银子处理给小妾母子,立下案状永远不准再争斗。秦令可以说是巧妙索取钱财的人了。
附:将乐县的万安寨有一位张孝廉,贪婪而且放纵,极力侵占盘剥乡里邻居,以增加自己的利益,人们不敢违背他。张孝廉家里本来贫穷,后来于是骤然富贵了,靠着溪边建筑了房屋,楹栋相连,曲曲折折,方形亭子上,雕刻着阑干,用双层台阶建构,特别奢侈。没有多长时间,张孝廉进谒被选为蜀中的县令,但在半路病死了,家业随即因此破败了,今天的房屋属于我的乡邻夏生。而张孝廉的一个儿子,反而依附夏生居住,做奴役一点也不知道惭愧。我于丁酉年间经过夏生的家里,见张孝廉的儿子奄奄一息,处境冷落,琐头琐尾的样子,心里感叹,因此坐在方亭里写诗说道:“九曲池塘活水流,雕阑面面俯清幽。半生心力经营尽,好与人间话鹊鸠。”总之是为了记述这件事实。
江州人朱原虚有诗文的名声,他父亲死时,两个弟弟年纪幼小,朱原虚偷偷藏起父亲所遗留的十多筐子绫罗绸缎,两个弟弟流荡在外居住。朱原虚参加乡试多次不能考中。偶而一天请人扶乩,神仙用笔写道:“何处西风夜卷霜,雁行中断各悲凉。吴绫越锦藏私箧,不及姜家布被香。”朱原虚得到扶乩的诗,惊慌害怕,叫来两个弟弟回家,将箧里的凌罗绸缎平均分配了,规劝勉励他们努力求学,后来兄弟几人都考取了进士。
有个叫薛包的人与各个弟弟分配财产,另外居住,他分配时要荒废的田园屋舍,说道:“这是我小时候所整治的。”收留下年老的奴仆婢女,说道:“和我共同处理事情时间长了,其他人不能使用。”分配要损坏的用具物品,说道:“我平常所使用,已经习惯了。”后来他的弟弟们都财业衰败,而薛包又帮助赈济给他们。
林退斋临去世时,子孙们跪在他的膝前边请示道:“父亲用什么来训导后辈?”林退斋说道:“没有什么话,只是让你们学会吃亏。自古以来的英雄,只是因为不能够吃亏,贻害了多少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