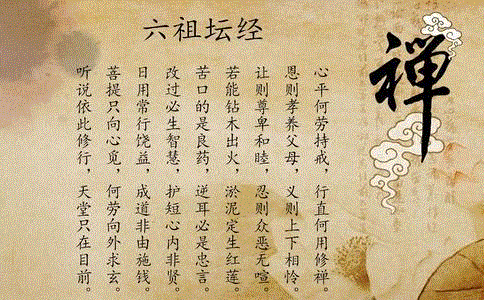白居寺壁画:走向成熟的藏传佛教艺术
发布时间:2024-06-12 03:04:00作者:六祖坛经全文网江孜县白居寺的吉祥多门塔
白居寺错钦大殿里的菩萨塑像
白居寺,藏语意为 吉祥轮上乐金刚鲁希巴坛城仪轨大乐香水海寺 。一般简称 班廊德钦 ,即 吉祥轮大乐寺 。关于白居寺创建的时间和白居塔的设计者,目前的藏史资料里说法不一,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白居寺的群体建筑并不是同一时期一次性完成的。
圆满庄严的建筑载体
初见白居寺,它在7月的夏日午后显出一种如断臂维纳斯般的残缺美。除塔、寺和部分围墙外,白居寺现仅存有5个扎仓和佛殿,其他建筑均已遭毁坏,或被改作他用。在白居寺错钦大殿一层右边,护法神殿的佛龛上摆放着四五张摄于解放前的黑白照片,那上面,位于江孜镇宗山脚下的白居寺,东南北三面环山,西面临水,整个建筑由白居寺大殿、吉祥多门塔、扎仓,近30个佛殿和围墙四大建筑单元组成,形成一座宏伟巨大的寺院建筑群,远比现在气派。这是相对完整的白居寺留给我们的最后记忆。
白居寺,藏语意为 吉祥轮上乐金刚鲁希巴坛城仪轨大乐香水海寺 。一般简称 班廊德钦 ,即 吉祥轮大乐寺 。
关于白居寺创建的时间和白居塔的设计者,目前的藏史资料里说法不一,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白居寺的群体建筑并不是同一时期一次性完成的。措钦大殿的修建要早于白居塔的修建。一般认为,白居寺(主要指措钦大殿)始建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即1390年,由后藏大贵族帕巴贝之子贡嘎帕为祭祀先祖修建 桑波仁波林 佛殿,初名为 江热寺 。1414年贡嘎帕之子曲吉 饶登贡桑帕为了孝敬母亲,为其还愿,捐资礼请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克珠杰主持扩建佛殿、僧舍,由此兴建了白居塔,自此改名为 白居寺 。现在,全寺分属格鲁、噶举、萨迦三个教派,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是江孜县境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作为白居寺主体建筑之一的措钦大殿,在其形制和建造手法上具有典型的藏族建筑风格。大殿坐北朝南,共三层,底层为经堂部分,殿门后为前室,右为护法神殿,左为一小佛殿。过前室为大经堂,有立柱48根。大经堂之东为法王殿,西为金刚殿,东西配殿对称统一。大经堂的后部为后殿,有8根立柱,供大菩提铜造佛像。
据说,在白居寺建筑群中,蕴含有18种美好和圆满的建筑美学理念,而措钦大殿为 十八圆满第一项 。在措钦大殿完工后,寺主饶丹贡桑巴还为该寺修建护持的大围墙,每一边长280步弓,围墙上建有20座角楼作为装饰,开有6个大门,并在墙外四周种上了树木。从这里可以看出,主体建筑大经堂与辅助建筑佛塔,以及围墙、角楼和四周的树木之间,形成了有序的空间布局,错落有致,和谐统一。
在藏学研究中心专家熊文彬看来,藏史中用 设计圆满 来评价白居寺错钦大殿,实际上是认为大殿体现了佛教建筑意义上的 圆满如法 。而 圆满庄严 一词,在藏族艺术史上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概念。这一建筑美学标准,早在松赞干布修建布达拉宫时就已明确提出,且作为评判寺院建筑或是宫廷建筑是否完美的标准之一。
当然,作为宗教建筑最高的美学理想,仍在于通过象征的建筑形式,无声而具象地弘扬宗教教义,感化熏陶、培养和转化进入这一神圣空间中的广大信众,并使他们的 虔信之力迅速建成 。这便是宗教建筑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或是最终目的。
白居塔位于措钦大殿右侧,与大殿遥相辉映,是整个白居寺建筑中最重要、最富于象征意味的建筑物。白居塔的修建晚于措钦大殿,从1427年佛塔奠基,到1436年白居塔完成泥塑、壁画和装饰,前后历时10年。从佛塔类型上看,白居塔的建筑形制为藏式 噶当觉顿 塔风格。全塔共九层,塔瓶以下共五层,一层下为塔基。一层至四层,四面各建佛堂。外形上呈四面二十角(又称四面八角),每层逐渐收缩,层叠而上。塔瓶为圆形柱,直径20米,内有佛殿四间(即第五层)

白居寺内的壁画
无论你站在何处,都能感受到白居塔曲折多变的外形轮廓:阶梯式收缩的五层塔座,覆钵式的塔瓶,以及渐次成梯形的 十三天 塔刹,不但形成了各建筑部分鲜明的对比,而且生动体现了一种建筑艺术的韵律感。
熊文彬说: 白居寺作为塔寺合一的建筑典范,在结构布局及象征手法的运用处理上,完美传达了佛教抽象的哲学理论。在这里,曼陀罗式的立体构图,十分严谨地象征了教义的不同内涵。例如:佛塔上的莲花象征六随念;塔基象征十善之土地;塔阶象征四随念;塔藏象征法力;塔瓶象征菩提心;塔珞(花蔓)象征圣者及菩提三十七道品;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上的法轮,象征十力和三近住;观音咒藏象征大慈大悲和十六大空合二为一;塔伞和遮雨檐象征智慧双足;滴雨檐象征事业兴盛;太阳和月亮象征先知。如果说,建筑最能体现一种哲学思维的话,那么白居塔和早期的桑耶寺,以及以曼陀罗为原型建构的寺院建筑,可谓充分体现了佛教的宇宙观。
站在白居塔高处向寺院入口方向远眺,能看到不远处依山而建的江孜古堡。吐蕃古代王国坚耸危厄的古代城堡式的宫廷建筑在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从12世纪左右,已经开始与寺院建筑走向结合。熊文彬说: 无论是元代扩建的萨迦寺和夏鲁寺,还是明代兴建的白居寺和扎什伦布寺,政权和神权在宫殿和寺院合璧的民族化、地方化建筑艺术中得到集中体现。
宗教仪轨之外的创作自由
白居寺的壁画,主要保存在措钦大殿和白居塔中,位于措钦大殿后山上的仁定扎仓也保留有一些壁画。从时间上看,措钦大殿内的壁画,比白居塔内的壁画相对要早。
措钦大殿从第一层到二、三层均有不同题材的壁画。壁画是依照殿堂的礼拜和修行功能绘制的,故而其布局与构思,显得严谨周密,不仅符合佛殿礼拜、诵经的建筑要求,同时也遵守了佛教仪轨和律制。
措钦大殿内的壁画,有的清晰可见,有的被香灯熏染得模糊不清,有的因殿内漏雨被侵蚀得漫漶斑驳。据藏文史料,措钦大殿经堂壁画题材主要有:释迦牟尼佛、燃灯佛、弥勒佛、释迦牟尼八大弟子等。一般而言,经堂内的壁画篇幅较大,气势宏伟,释迦佛结跏趺坐,两侧分立八大弟子,佛为中心,由此展开布局,突出了世尊与弟子的关系,也符合绘画的透视关系。大经堂后壁,右侧绘制有阿底峡尊者像,旁边有巴买久仲坐像;左侧壁画是宗喀巴大师像,依次绘有克珠杰、弥勒佛、布顿大师的坐像。
在白居寺壁画中,人物始终成为画面表现的重心,上至佛果遥远的诸佛菩萨,下至尘世今生的凡夫俗女,组成了千姿百态的佛画世界。不过,白居寺壁画中的人体量度和早期的三经一疏(大正藏藏文版《大藏经》143卷《医方明 工巧明》第三部分中的《佛像如尼拘落陀树纵广相称十拃量度经》、《正觉佛所说身影像量释》、《画相》和《身影像量相》四部经典)量度和比例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佛像创作过程中,以现实中的人体及其相貌作为范本创作,藏地艺术家对印度佛教美学体系中的人体比例和相貌都进行了创造性发展,融入了民族的审美倾向,拉开了民族化佛教艺术的序幕。到十四五世纪白居寺创建前后形成了一系列人体比例和造像理论流派。
早期造像量度中高大、苗条的身躯在白居寺佛像造像中变得相对粗壮、短小和结实,更加富有力度。除吉祥多门塔一层西大殿净士殿和东大殿兜率宫殿壁画主尊无量寿佛和弥勒佛身边的两身胁侍菩萨等为数不多的菩萨尚保持着较为修长、苗条的身躯外,绝大多数人体比例都逐渐相对缩小。 熊文彬认为,这种人体比例的变化正是佛教及艺术逐渐走向藏传佛教艺术化的结果。
与大多数壁画一样,线条和色彩处理构成了白居寺壁画技法的两大基本内容。色彩和线条的反复处理和组合贯穿壁画创作始终,两者的穿插和组合通常包括壁画起稿、设色、晕染、勾色线和上金等几大重要技法程序。因此,线条勾勒的技巧和设色直接影响到壁画的艺术水平。
无论在青海还是西藏,我没有见过画师为寺院创作壁画的过程,但在热贡,我亲眼见到扎西当周刚勾勒出初步线条的唐卡以及他的徒弟为唐卡设色的过程,正在勾色线和上金的徒弟们和唐卡的距离在毫厘之间,为的是每一笔都精细到毫无瑕疵。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文华也是著名画家,在他看来,壁画和唐卡是绘画艺术的两种不同形式,从绘画语言上看,两者是一样的。 这些画师以家族或村落为团体出现,学同一画派的上师,之后分出两拨人,手相对粗一点的画壁画,精细一点的则画唐卡。唐卡只有区域画派的不同,而壁画往往综合了不同绘画团体的很多风格。
白居寺壁画中的线条和晕染十分有特点,它不同于内地的单线平涂,以线描造型为主的古代国画,也不同于以晕染造型为主的西画,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将两种技法融为一体。吉祥多门塔一层大力明王殿中的大力明王、马头明王殿中的马头明王和不动明王殿中的不动明王等护法神的形体塑造中,晕染和线描的处理堪称白居寺壁画中的佳作。尤其是上下肢和面部、腹部的晕染,不仅表现出骨节的转折和肌肉变化,使肌肤富有质感,更重要的是通过晕染加强和突出了四肢造型的力度和气势,与健劲的轮廓线紧密配合,有力地刻画出护法神内在的气质。
也许是青藏高原蔚蓝的天空、青翠的草地和皑皑雪山之间色彩的和谐和巨大反差启迪了高原艺术家们对色彩独特的感受和处理能力,和谐和对比构成了白居寺壁画色彩运用的一大特色。白居寺壁画中,通常运用浅蓝或灰褐色作底色,除偶尔用绿色外,一般为冷色调。然后根据造像仪轨中规定的不同身色来巧妙处理背光和其他装饰性纹样,利用色彩和谐和反差的属性来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
藏地传统壁画的颜料都是天然矿物质,他们发明了用青金石提炼蓝色,用珍珠做白色,用珊瑚做红色,用松石做绿色,用赤金做黄色的 五原色 ,分别象征蓝天、白云、火焰、河流和土地。 罗文华说,矿物颜料色彩纯正,有深度。 比如用绿松石,可以提炼出十几二十几种不同绿色,而不同画师调配出的颜色也不同,这样的颜色画上去可以呈现出特别丰富的过渡色。现在唯一比过去好的是金色,因为过去的黄金用量大,没有现在这么纯。
与汉地比,藏地的佛教艺术因为要遵循的仪轨多,给画师们自由创作的空间并不大。但即使如此,13世纪起,西藏壁画逐渐形成了各具风格的 噶玛嘎哲 、 堪日 、 门唐 三大画派。罗文华认为,开创独立的画派之后,在尊神主体不可变化的前提下,藏地的传统壁画在两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一是布局的改变。早期的唐卡、壁画,几乎可以画出格子来;而后期,山石、树木甚至人物也可以错落分布,打破了以前单纯几何形的布局。二是艺术手段的变化,比如色彩变化、背景元素的变化。画一个极乐世界,屋檐装饰、青山绿水都是可变的。
诸佛菩萨和坛城中佛国世界神灵们的色彩在造像量度经典中有明确的规定,同时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和宗教内容,因此一般不能凭画家对色彩的个人感受随意发挥,必须遵循造像仪轨规定敷设色彩。但尽管如此,也并没有限制白居寺画家们色彩能力的高度发挥。
白居寺内景
吉祥多门塔一层回遮殿八臂白伞盖佛母壁画的用色体现出白居寺壁画色彩处理和运用的一般原则。这铺壁画底色为浅蓝色,主尊为白色,在巨大的背光顶上艺术化的菩提树龛造型中运用红绿色彩处理红花和绿叶,菩提树边缘绘一道白色云彩,与底色形成强烈对比,烘托出菩提树造型。背光为一片跳跃的红色,与主尊背光左右的底色和主尊身色也形成鲜明对比。身光和头光的处理又与背光色彩形成反差,为一片冷色调的蓝色。主尊上身为白色,下系绿色基调的短裙,双肩飘垂着红色的天衣,头着金黄、红色和蓝宝石镶嵌的三叶宝冠,双耳、项脖、双臂和双手及脚腕分别佩戴着金色的耳环、项链、手镯、臂钏和脚镯。毋庸讳言,装饰品中的红、绿、金色又与身光、头光中的蓝色彩形成反差,有力突出了人物形象。正是这种利用色彩不同的冷暖属性和饱和度的层层铺陈和渲染,形成了白居寺壁画色彩运用和处理的突出特点。
萨迦,夏鲁遗风
白居寺壁画风格最早可以追溯到萨迦寺壁画。萨迦寺创建于1073年,是后弘期西藏修建较早的寺院之一。在元代,由于萨迦派政治上得势,宗教势力不断扩大,不仅扩建了北寺,而且增建了南寺,使萨迦一跃成为元代西藏最大的寺院。
意大利著名藏学家G.杜齐对萨迦寺壁画有一段评论,认为贡嘎仁钦时代,萨迦寺早期壁画受到了印度、尼泊尔和中原内地艺术的影响,这可能同元代八思巴召请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等到萨迦建金塔与汉族、蒙古族直接参加南寺修建有关。萨迦寺壁画因此在吸收中亚和中原内地艺术风格的同时,开始形成独特风格的创作,且影响到了后来白居寺壁画的创作。
罗文华说,白居寺大部分壁画都是坛城,萨迦派不仅在后弘期内以宏传密宗坛城闻名,而且也以擅长坛城绘画而著名。据白居寺壁画题记和《江孜法王传》记载,吉祥多门塔五层东无量宫殿北壁根据瑜伽续摄根本续第一品绘制的以金刚界大手印为主的根本大坛城壁画就是根据萨迦派坛城仪轨绘制的。与此同时,结合杜齐根据布顿著作对白居寺壁画坛城进行的分析都表明,白居寺坛城壁画内容也受到了创建于11世纪初期的夏鲁寺壁画的影响。
布顿大师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西藏佛学各方面几乎都有著述,学识十分渊博。他不仅编纂了大藏经《丹珠儿》目录,而且对西藏十三四世纪以前所传的密宗典籍进行了分析、整理和注释。现代著名佛学研究家王森先生评价他是西藏佛教史上 第一个想把密法系统化的人 。他撰著的系统化的坛城十万尊像仪轨就是夏鲁寺坛城影响白居寺壁画坛城的主要标志。
G.杜齐教授在《印度 西藏》一书中根据布顿大师撰著的坛城尊像仪轨的有关著作对白居寺壁画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吉祥多门塔佛殿中大部分坛城壁画的主尊、眷属及其身色、标帜和方位都与布顿著作基本吻合。
实际上,夏鲁寺对白居寺壁画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坛城内容上,还体现在艺术风格上。
从江孜前往日喀则寻访夏鲁寺的过程并不像寻找白居寺那么轻而易举。导航并不能像搜索白居寺那样轻松就定位到夏鲁寺的具体方位,我只能找到距日喀则东南30公里的甲措雄乡夏鲁村,在那条遍布油菜花田的岔路口徘徊、错过。义无反顾地进入后,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的,夏鲁寺就坐落在雅鲁藏布江南岸与年楚河交汇处的下游地段 夏鲁河谷,蜿蜒的夏鲁河由南向北从夏鲁村和夏鲁寺身后缓缓流过,汇入年楚河。
据《后藏志》等诸藏文史籍,夏鲁寺从11世纪中叶由介尊 西饶迥乃建夏鲁金殿开始,到古相 贡噶顿珠和布顿大师时期为止,其间经历了三次不同规模的修葺和扩建。第一次大约发生在1290年的古相 贡波贝时期,第二次大约发生在1306年以后的古相 扎巴坚赞时期,第三次为古相 贡噶顿珠和布顿大师时期。这三次扩建中,古相 扎巴坚赞时期的规模最大,夏鲁寺现存的主体建筑和大部分壁画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
诸如集会大殿一百铺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和二楼回廊的《须摩提女请佛》等壁画都是在扎巴坚赞时期绘制的。这些壁画在风格上都体现出来自印度、尼泊尔和中原内地艺术风格影响的痕迹。集会大殿一百铺本生故事棋格式的方形构图,胁侍菩萨的三折枝造型,高僧大德的着装和红色底色背景的表现,尤其是《舞蹈家本生》人物造型中较为明显的南亚人特征都传递出印度波罗艺术的气息。而二楼般若波罗蜜多佛母殿回廊朝佛行列中比较明显的元代中原着装和琉璃歇山顶建筑纹样的描写,则体现出中原艺术的特点。但无论这种影响是来自印度、尼泊尔、中原,还是来自元朝宫廷中受阿尼哥影响的宫廷佛教艺术,都掩盖不住夏鲁寺壁画中悄然出现的一种具有内在力度刻画、朝气蓬勃新风格的形成。 熊文彬说。
根据白居寺壁画画家题记来看,夏鲁寺对白居寺壁画风格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拉堆地区和乃宁地区的艺术家来实现的。
白居寺所有壁画和塑像主要由后藏西北的拉孜和当时江孜的乃宁两个地方的艺术家队伍创作完成。江孜西北地区参加白居寺壁画创作的画家除来自拉孜外,还有一部分画家来自觉囊地区。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廖旸告诉我,白居寺壁画从整体风格看十分接近,仔细观察,仍各具特点。乃宁、尼木画家笔下的壁画与拉孜、觉囊笔下的壁画相比,色彩更加富丽和谐,菩萨秀丽典雅,纹样繁缛华丽,给人清秀柔美的审美感受,与拉堆艺术家创作的质朴自然、简洁明了、富有力度的风格相映成趣。 与后期格鲁派寺院哲蚌寺、色拉寺壁画相比,白居寺壁画中少了一些富贵的金碧辉煌的装饰追求。例如白居塔中的药师佛像,布绘于花蔓之中,蓝色的身躯、红色的袈裟、金色的火焰光纹组成背光色彩。左手托钵、右手持印的药师佛,似从天降一般,庄严妙好。其壁画风格,仍具有早期单纯古朴的画风。
尼木与乃宁所处地理位置相同,同处于拉萨、后藏和山南交界地带,乃宁、尼木画风与拉孜、觉囊画风一道构成了白居寺壁画艺术的主要潮流。此外,白居寺壁画还体现出中原内地艺术风格特点。在八思巴与忽必烈会见壁画下壁的供养人牧马场面,表现的是西藏牧歌式的游牧生活。一片空旷静谧的青草地上,点缀着悠闲自在的马群。一匹马低首下俯正在悠闲吃草,另两匹马翘首相望,似乎觉察周围有所动静,小马驹惊吓得从身旁匆匆逃离。4位牧人头戴圆帽,足着皮靴,身着长袍,盘腿而坐。左面两位正回头张望,似乎有人呼喊;右面两位,正在促膝交谈。人马的造型和画面中动静的处理,以及刹那间凝聚的心理状态刻画得极为精妙。人和马的造型都十分写实,甚至连人的须发和马鬃都清晰可辨,有工笔画特点,让人联想到元代画马名家任仁发。而在岩石,树木的刻画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具有内地山水画特点的皴擦点染的特征。
熊文彬说: 中原艺术风格的影响大体来源于两个渠道。第一种渠道来自萨迦,夏鲁寺壁画。也就是说,白居寺壁画在接受萨迦和夏鲁寺壁画风格影响的同时,接受了这两个寺院中中原艺术的某些风格和表现语言。另一个渠道则直接来自内地艺术,确切地说,主要来自明代宫廷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
白居寺二层的罗汉殿,门口画的四大天王完全是独创性的,融合了汉藏元素,颜色以淡黄为主,有强烈的宗教情感。而在此之前的壁画,背景色都是强烈的纯黄、绿、黑、红,没有过渡色。壁画里的树也是有点卡通化的,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让我想起达利的名画《柔软的钟》。 罗文华说,从夏鲁寺壁画开始,藏地壁画从崇尚宗教的、色彩浓艳、柔媚的印度、尼泊尔风格走向浓淡相宜,融合多种艺术风格的西藏氛围。延续至白居寺,经常出现一些创造性因素, 西藏的艺术家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色彩造型清楚,随意而富有创造性 。
如果说夏鲁寺的壁画是藏传佛教艺术早期古典复兴派的代表,那么,百年之后,白居寺的壁画则以强烈的西藏本土自觉性和自信心,在汉地艺术的支撑之上,从清新的世俗艺术和宗教的肃穆感之间找到平衡,开启了近现代藏传佛教艺术独立发展的时期。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或“中国西藏网文”的所有作品,版权归高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何媒体转载、摘编、引用,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