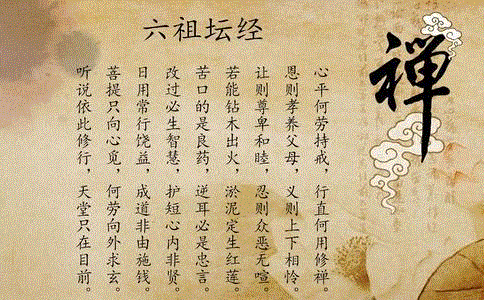六祖坛经
发布时间:2023-07-11 10:16:33作者:六祖坛经全文网《坛经》导读
作者:中禅
《坛经》是“具有中国特色”佛教——禅宗代表性经典,由唐代慧能大师(638——713)讲述,学生记录整理而成。在佛典中,中国祖师的开示被后人称为“经”的仅《坛经》而已——由此可见其独特高尚地位。《坛经》不仅是一部中国佛教特有名著,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品之一,以其深远影响,对世界文化也作出了贡献。
慧能大师是中国禅宗真正意义上的创立者,他首建“曹溪宗”,后“一花开五叶”,发展成禅门“五家七宗”。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坛经》里,这对中唐以后的佛教和后来儒家宋明理学,都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汉传地区佛教宗派的主流,后传至朝鲜、日本,近代又向欧美发展,表现出强大生命力。
认识《坛经》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应了解其产生的必然性与社会文化背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及禅宗兴起,以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从而彻底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坛经》是其思想代表。
因此,本文分两部分:一、简述有关《坛经》产生的历史背景;二、介绍《坛经》正文,依流传的“宗宝本”内十个章节,提要叙述。
该节包括以下内容:1、简述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2、中国式佛教——禅宗崛起;3、禅宗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及本土化;4、《坛经》特点;5、《坛经》的几种版本;6、学习《坛经》之目的。
1、简述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
中国佛教发展的历程,即中华文明以特有之博大胸怀,接受伟大外来佛教文化的过程。并将佛教融入自己民族文化之中,相互磋磨汲取,形成了彻底本土化的独特的“中国禅宗”。
佛教在中国发展大至分两阶段,一是吸收印度佛教阶段;一是佛教“中国化”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六七百年间(约公元147年安世高始译佛经,至公元664年玄奘翻经止),基本上是“原汁原味”地翻译佛教经典,接受教义。隋唐时代,随着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的出现,已渐渐形成了佛教适应、汲取、结合中国原有的儒道文化背景,形成了义理精确,具有“中国特色”表现形式的“本土宗派”。
隋唐是中国文化对佛教接受与自立的转折时期,即以唐贞观年间,玄奘大师(596——664),从印度留学归来为标志,表明“学生时代”结束,已逐步形成中国大乘八大宗派。计有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都是中国本土宗派,较早形成的成实、俱舍宗为大乘附属之派别。
中国是文明高度发达的世界性大国,以儒道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求同存异的泱泱大国胸怀,故印度高僧说中国人有“大乘气象”,而中国历代高僧大都有深厚之儒道文化素养。就八宗而言,三论、律宗、唯识、密宗之印度气息较浓,而天台,华严、禅宗之中国民族风格较著——在印度较重门派知见,多辩论,而中国则多雅纳包融,故在印藏地区胜行义理争辩是难得找到这种文化气氛的。

有隋一代,智者大师(536——597)首开天台宗,以“一念三千”说明实相;以“空、假、中”的“三谛圆融”阐明止观定慧之学;以“五时八教”对释迦教化作了中国式的全面判解,以有别于印度传统的“三时教”,成最早的一家之言。
唐初吉藏大师(549——623)创三论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纲领,继承龙树、鸠摩罗什的印度大乘中观思想,提出“二藏三论”(二藏即声闻、菩萨二藏)的判教主张。
唐代玄奘大师归国后创唯识宗,透彻昭示“三界唯心,万物唯识”宗旨,并译经展现印度佛教全貌。以《瑜伽师地论》、《俱舍论》、《大般若经》为中心,揭示印度佛教发展之脉络,此治学气象,为印度学者所无。尤其是对《成唯识论》之编译,成为唯识学的代表作,其立“真唯识量”的学术成就,为印度因明学中所无,实为首创。
法藏大师(643——712)即贤首国师,虽继承杜顺、智俨《华严经》学统,实为华严宗真正创始人,他借鉴了天台、三论及瑜伽学说,特标“别教一乘”、“法界缘起无尽”说。融涅槃生死、真俗本末、原因后果等种种二相分别,尽纳入“法界缘起”观,点出“因赅果海,果彻因源”之宏大精深菩萨境界,依人们可能悟入的理境,达登峰造极。
2、中国式佛教——禅宗崛起
禅宗之创立,虽肇始齐梁,但在盛唐之前,皆由个人单传,并未普及于社会。由印度第二十八代祖师达磨,将释迦牟尼佛亲授之“拈花正宗”传入中国。相传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大众默然不解,唯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领悟奥旨,佛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并付金襕僧伽袈裟为信物。故禅宗立宗要旨,在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用一切语言概念、逻辑思维来分别揣摩是无益的,是不能把握的,唯经过内心自省以达豁然“顿悟”(此故事见于大藏经中《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然而,禅宗真正的开山祖师应该是《坛经》作者慧能。由他肇始“一花开五叶”,全面向社会推广禅宗。禅宗得从繁琐哲学中脱颖而出,倡导“当下”心态的自觉,提倡“受用”,于身心有实际的良性作用,从分析名相、辩驳教理、引典劳碌等众说纷纭中解放出来,独树“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大旗,倡导“直指人心”的便捷方法,将全部佛教真谛汇归于对现实自心之“觉受”,摆脱了一切教条羁绊,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从生活中直接体味身心性命,体味人生宇宙中佛法之真谛。在师徒授受方面,更在日用动静、起心动念、嬉笑怒骂中激扬指点,在杀、活、纵、夺中实施——此种作略虽在马祖后大见开展,但初显端貌,则全在《坛经》的包蕴之中,这不但对佛教具有革命性,在世界思想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心理实践体系。
会昌二年(842)唐武宗推行灭佛运动,至会昌五年,拆毁大中寺院四千六百所,小庙万余处,还俗僧人二十六万多人。这是中国佛教在历史上的关键性转折时期,形式上的灭佛运动,在历史上反而促进了禅宗——佛教的精髓,日后大规模地,乃至面向世界的发展。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历史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禅宗,中国佛教是难以承受唐武宗灭佛运动打击的(当时印度佛教由于外部打击而一蹶不振,逐渐步入消灭。西藏佛教也由于郎达玛[838——842]的打击而一时衰微,经历长达百年的“黑暗时期”,中亚及新疆佛教从此也近绝灭)。在那次遍及全国(其实也世界性的)的灭法运动中,佛教在中国,除禅宗外的所有宗派几乎大多覆没了。这些宗派失去了寺庙的依托,失去了寺院经济和经典文化的支撑,就没有了生存能力(印度后期佛教尤其如此)。事实也是这样:唯识、三论、天台、华严、律宗和密宗在那次打击后一蹶不振,有的永远消失了。而六祖慧能大师开创的禅宗(南宗顿门),不仅安然度过法难,反而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遍布全国,取得了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迄今为止,汉传佛教的主要寺庙,无一例外传承禅宗法系。如“上有文殊宝光(四川成都文殊院、新都宝光寺),下有金山高旻(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即为“禅宗寺院遍布天下”的代表性说法。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也是一个奇迹。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禅宗的核心道场,归根结底是安置于个人的内心,是个人对自己现实思想深沉的反省,从而才有可能在人群中获得了无限广阔的普遍性与极大方便的现实性。这种内心的道场,不再受时间、空间、职业、贫富及学识多寡限制,也是无法限制的。禅的核心焦聚在此刻、此处之“现实心态”——“直指人心”,苦至狱、病处,乐至名利场,人人皆可方便自省,回心向道。故禅宗的优越表现在广大的“群众性”,无以伦比的“现实性”,与最深刻的“思想性”(心地法门)。所以,如果没有慧能大师开创的禅宗,佛教在中国的生命能否延续至今就成了问题。历史本身也表明了,唐末灭法一千多年来,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主要是禅宗传承(亦并行净。至于禅净合一,多归于“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禅法理路)不仅在历史上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且如此绵延发展,传遍日本、朝鲜、越南,近代且有发展至欧美的趋势。
玄奘大师的唯识宗在中国只传了四代(至近代方多研究者),何以如此优秀甚深的传承就无以为继?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方便可行。印度式的经院哲学大多繁琐,皓首穷经尚难通达义理,更惶论抉择精义而行?学者尚难穷究,社会士大夫及群众更望尘莫及。三论宗等亦如此,而一般密宗对经济有所要求,灌顶仪轨亦很繁难,对广大社会群众,自有不便,故以难传——当然也有唐武宗灭法因缘等社会因素。
诸宗消沉,禅宗独盛的事实,表现出禅宗能经受严酷社会淘汰的顽强生命力,这是由禅宗特点决定的,禅宗要旨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简明扼要,朴实可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提倡行住坐卧、搬柴运水皆可参禅,乃至后来马祖(709——788)提出“平常心是道”,促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觉悟。由于不背寺院经济、经典文献包袱,唐武宗灭佛摧毁了全国大量的寺院与典章文献,却不损禅宗一毫毛。由于禅宗安道场于个人心地,方法是自心反省,便捷可行,又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在基本原则上可以协调,甚至更能突出其某些心要(在下文还要专门述及),故在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上,获长足进展,易于为士大夫接受,逐渐获得巨大的社会普及性。宋明以后,禅的思想已慢慢浸入社会生活,成为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
禅宗本身已含摄了佛教全部精义,不论显密、世出世法皆可在个人心性修养内融汇贯通,富有蓬勃鲜活的生命力。一个禅者就是一粒种子,无论在何等环境下皆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皆可于“现身说法”的语默动静中产生社会作用。这些特点,较其他诸宗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故千多年来,禅宗成了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
“禅”本来是印度语译音,静虑之意。义为通过修行,扫除精神杂质,回归到心地本分的觉悟。印度禅学只是一种修行方法,与戒学、慧学是平等的,单立为学科,这还不是中国的禅宗之禅,在印度佛教里是没有禅宗的。“禅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禅宗既然是佛教内一宗派,何以自称“教外别传”呢?因禅宗产生于佛教鼎盛的盛唐,当时天台、唯识、华严、三论等宗派在学术上极为繁荣,是中国佛学的黄金时代。禅宗认为其他派别都主要通过文字语言传教,多用逻辑思维来阐扬教理,故称“教下”;而禅宗自称“宗下”——万法归宗之义。禅宗认为语言逻辑不足以表达究竟真实义,且有教理愈繁,实义益晦之嫌,虽学富五车,而直接证悟者甚少。禅宗针对此状况,特别强调了在自心中的实修体验,要求在自省中觉悟,了脱生死,当下解脱,顿悟成佛,即禅宗认为的佛法归宗之处。在法统传承上,慧能大师虽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发起者,但也上溯至佛陀,单传廿八代于达摩,再下传至中国第六代祖师慧能,再由慧能造《坛经》,乃至“一花开五叶”,建立禅门“五家七宗”向全国乃至最终向世界发扬光大。
3、禅宗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及本土化
现在有的学者认为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甚至认为禅宗的优点,在儒学本来就有。其实不然,禅宗的根本目的在于彻证“无生法忍”境界,这是印度佛教思想精华所在,为中国本土文化未见记载,而禅宗在“顿悟”体验中实证此事,毫无疑问是纯粹佛教思想,然而却在中华大地开放出光明璀璨的花朵。
同时,也有人对“中国化佛教”不以为然,怀疑其是否“走味”,认为既是佛教,当奉持印度形式。其实,佛教精要在“无生法忍”之“顿悟”实质,并不在表面形式,而任何外来文化的传播,都不可脱离接受地域的传统特点,否则就不能生根,就不能有机融合。必须在当时当地的民族文化习俗背景中求得发展,在求同存异中获得本土特色,若与当地民俗不合,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是缺乏拓展空间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完全脱离本土文化与民俗背景是不现实的,很难融于民族文化深层血脉中,然而禅宗却做到了这一点。佛教讲缘起,原有民族文化的存在,包括儒道思想,本身就构成了佛教发展缘起的条件,所以说禅宗及至天台宗、华严宗本来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尚与光荣,是中华民族吸收并消化了印度文化后绽放的花朵。若不懂禅宗(并包括华严、天台的核心思想),那么研究从隋唐至宋元明清的中国文化脉络就根本深入不了(如不理解《华严经》“一多相容”思想,就很难理解后来宋儒朱熹[1130——1200] “理一分殊”、“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的理念,在学术界,这被认为从前者脱胎而来)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系统,骨子里却是禅学。儒家所谓孔门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永执厥中”,也可纳入的理念,可以认为表达了真俗不二,及注重现实心理体验的理趣;在《中庸》里,有“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慎戒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表现了儒家“思孟心学”的特色,敬慎反省“当下”之心境与禅宗修行方法不违悖,更有《论语》中孔子名言,“吾道一以贯之”,这更是明确的“心行一元化”思想,与佛教“心一境性”、“一行三昧”也有相通之处。然而,这些在汉以后就沉寂了的“现实主义思想原理”,于唐宋后,却在禅宗“注重当下”巨大影响诱发下,又重新活泼起来,恢复了生命力,并开启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相互激扬的生动局面,为一度僵化于“章句训诂”的儒学,带来了新的发展生机。儒学的一些精神领袖,如王阳明(1472——1529)等人,虽以隔代远承思孟心学自居,高标“至良知”修养,却自称“居士”,并要求学生研读《坛经》,由此可知禅宗与《坛经》在当时思想界巨大的影响。宋明以降,上至皇上、达官显贵士大夫,下至一般儒生庶民,多以“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自居。禅宗思想与儒道思想协调,在中华大地上有了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与社会文化基础。唐代道家著名人物吕岩(吕洞宾,798——?),也将《心经》与《金刚经》等与禅宗有关经典,纳入道家心性修养的体系中;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义为:可言说之道,非真“常”之道;可言说之名,非真实之名)也揭橥了类似“离言说名相”之“道”,也可与禅宗“不立文字”、“言语道断”的原理相互发扬,形成新的影响。至明代,憨山大师(1546——1643)以佛法禅宗观点著《中庸直指》、《老子道德经解》、《庄子内七篇注》等作品,对宫廷有相当的影响力。再传弟子藕益法师(1599——1655),也撰《周易禅解》、《四书藕益解》等,从社会文化背景的实际出发,协调了三教千年纷争,走求同存异,产生普遍社会效果,形成共同并存的中华民族主流文化,这也是佛教与传统文化高度融合的表现。追本溯源,都可以在禅宗提倡现实心性之学的《坛经》里,找到端绪。
在儒学重现生机的宋明理学中,不可否认,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禅宗的影响,若从中抽掉禅宗心性之学成份,即暗然失色。这样,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就讲不下去,变得无法认清其内在演化脉络。从唐末五代之后,禅宗心性之学就成了中国佛教主流与核心,在那时的中国,经历了严酷的社会淘汰以后,禅宗就代表着佛教。所以禅宗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专题,不了解禅宗,就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核心。

4、《坛经》特点
《坛经》有五大特点:
①简明化。高度浓缩了佛教宗旨与修行方法,直接了当地提倡个人当念反省自觉,顿悟成佛。“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及至佛地。”(《般若品》)又如在《机缘品》中,针对永嘉禅师所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直接挑明了佛教“本不生灭、本不动摇”的“无生法忍”悟道境界。
②中国化。六祖是中国禅宗真正意义上的开山祖师,前五代尚不具备此意义。从达摩传《楞伽经》,五祖传《金刚经》,还带有印度瑜伽和般若学派风格,而《坛经》虽完全融汇二经精要,并融入了《法华》、《涅槃》心要,使之彻底中国化、口语化,全变为中国风格。且《坛经》更著重“当人”自心实践,有不依赖外在权威之特点,亦与中国文化不特别崇尚鬼神,“敬鬼神而远之”,却高度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人文精神相符合,这也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最大特色,由此而建立注重现实的“人间佛教”,即人本位正法,现代又演绎为“爱国爱教”的佛教基本政策。
③普及化。《坛经》是唐代白话语录体,文风不像其他大经典雅深奥,也不像后来禅宗公案艰深晦涩,故适合大众学修。深入者自可领略宗旨,初学人亦自觉有个入处。学修禅宗,出家故然好,然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决疑品》)由此,可获广大社会群众参与,富于充沛生命力。
④革命化。禅宗一反印度外在形式的佛陀崇拜风格,而取佛陀教化的精神实质,崇尚吾人对自己心性觉悟,可谓一场认识上的革命,将“归依”重心转向当人“自心、自性”。“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忏悔品》)《坛经》这种高张当人“自悟”心性的革命风格,扫荡了一味外求的软弱性,也深契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弱化对外在权威神祇崇拜,重视现实人生之心性修养,张扬了人间佛教。
⑤实践化。《坛经》立意在现实可行,将最重要的真实道场安置于个人的“念头”,可谓方便之极。若人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省警觉,即不拘寻常种种心行、作务、在家出家,皆可参禅。大师说:“一行三昧(禅行道)者,即不拘一切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直接自觉当念)也……若言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草木),却是障道因缘。”(《定慧品》)又说,“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妙行品》)可谓为参禅者拓展出最大修行空间,赋予人们最充分的可行性、实践性,将佛教方便智慧的不二法门,发挥到极至。
5、《坛经》的几种版本
六祖在广州光孝寺受戒,印宗法师为该寺方丈,其受戒之戒坛为南朝刘宋时期译《楞伽经》的求那跋陀罗(393——468)三藏法师所建。六祖即于戒坛说法,由弟子记录,法海整理而成,是为《坛经》。现在流传的主要有四个版本:
①“敦煌本”——即法海记录本。清末于敦煌发现,或被认为是当时的传抄本。
②唐代惠昕和尚传下的“惠昕本”。
③宋代杭州灵隐寺名僧契嵩传出的“契嵩本”。
④元代广州光孝寺宗宝和尚又传出一个本子,内容最多,文字畅美,境界通达,是现在国内的主要流行本,称“宗宝本”。
6、学习《坛经》之目的
①认识禅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固有组成部分,和禅宗在历史上形成的深远影响的思想体系。

②通过对《坛经》的学习,获得对佛法的正确认识,通过自心反省、自心觉悟正知正见。
③使人们身体力行,用《坛经》来指导自己的思想行为,升华烦恼为菩提;变染污的环境为“三界唯心,万物唯识”的清净境界。